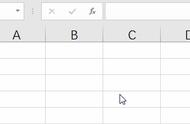贾红雨
原发:《世界哲学》2017年第1期
摘要:历史上的Reflexion概念所具有的三重意思——返回、反映和反思(自我认识)——及其在黑格尔体系中所具有的相互间内在且必然的关联,诠释了黑格尔理念运动的基本内涵: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描述的正是绝对者反映、显现于自身、返回到自身的过程,此过程亦是绝对者自我认知(反思)之过程。迄今为止,Reflexion一词的这三重意思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黑格尔体系的根本重要性,并未引起重视。相反,我们更多只是片面地跟随黑格尔而将作为思维活动的Reflexion简单地视为与思辨对立的两分观点。实际上,黑格尔那里作为外在观察者的哲学反思自身即是与精神或理念相平行且同一的自我提升、自我教育/形成之过程,而经过黑格尔根本性地改写了的思辨概念,标志的也绝非费希特和谢林的那种智性直观——一种直接性的自我意识或对绝对者的直接确信,思辨的根本特征恰恰是Reflexion所蕴含的那种基于否定性的自身关系之上的自我认知。
一、Reflexion概念史
词源上,Reflexion概念可以追溯到拉丁语reflecto一词。在西塞罗时代,该词只是一个日常词汇,其基本义指的是物体返回其运动的出发点。从基本义出发,人们也在各种转义上来使用该词,比如,激动情绪的“返回”意指情绪的克制(Cicero, De Oratore, liber I, 53; liber II, 312),潮汐的“返回”指季节的轮回变化(Apuleius, Florida, VI, 1),脚后跟的“返回”指其扭伤(Apuleius, Metamorphoses, liber XI, 27),精力的“返回”指其恢复(Apuleius, Metamorphoses, liber IX, 12)。在《为塞斯齐辩护》中,西塞罗也用该词来指注意力“返回”到荣誉之上(Pro Sestio, LXII, 130)。不过,这种相对罕见的、却极为重要的精神上的返回,在西塞罗这里指的只是注意力返回到之前观察过的外在事物,而日后的反思概念表达的则是主体将注意力返回到自身,对自身进行思考。尽管两者之间仅一步之遥,但从前者演变出后者,却要等到笛卡尔时代。
就内涵而言,精神的这种返回到自身,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过表述了。柏拉图在《查密迪斯篇》(Charmides 169d)中谈到“对自身的认知”,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 IX, 9, 1170)中论及“对思维的思维”。 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表述的这种精神的返回在新柏拉图主义者Proklos那里“获得了一个核心的体系性的位置,在术语上被固定为ἐπιστροφή (返回)”(Historischen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S.396)。但从词源上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我认知以及Proklos的ἐπιστροφή 与反思并无关联。
在奥古斯丁那里,ἐπιστροφή被翻译、替换成reditio in seipsum (“返回到自身”)。 早期一直被各种怀疑所折磨的奥古斯丁认为只有返回到人自身才能寻求到真理,因而他说:“不要向外走,而是要回到你自身”(Augustinus, 1991, S. 120f)。在论述这种将目光返回到自身以便反思、反省自身的时,奥古斯丁绝大多数时候用的术语是reditio in se ipum,reflecto一词只是偶尔被用到。就日后的反思概念而言,奥古斯丁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将reflecto确立为精神向自身的返回,而不是返回到某个外在事物那里。其次,笛卡尔那里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自我反思,在奥古斯丁这里就已经被确立为方法论,确立为寻求真理的前提条件。“然而当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并怀疑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的的时候,请你看看,你是否也会怀疑这一点:即你在怀疑。”(Augustinus, 1991, S. 123)奥古斯丁所表述的正是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需要注意的是,直到奥古斯丁时代,reflecto并不是直接被当作思维术语来使用的,其对“自我认知”这层意思的表达,始终要经过其基本义——“返回”的中介:注意力或目光返回到思维主体自身。
相较于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则经常用该词来表达思维或精神上的返回到自身。托马斯认为,人和动物都有的感性并不能达到自身认知:“感官能力并不返回到自身。”(Thomas, 2006, S. 82) 只有精神才能返回自身,才能达到关于自身的知识:“智性返回到自身,因而能理解自身。”(Thomas, 2006, S. 85)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述精神的这种返回即自我认知时,托马斯有时候用的短语是reflecto super se(Reflexion über sich),而并不总是reflecto in se ipsum (Reflexion in sich selbst)。后者从字面来翻译就是“返回到自身”,而super的意思是“关于”或“对”,因而把reflecto super se也翻译成返“返回到自身”就不合语法。所以,reflecto super se合适的翻译应该是“对自身进行思考”。这种情况说明,托马斯时期,该词开始慢慢被直接理解为反思,而不必总是要通过它的转义、拐个弯来领会自我认知这层含义了。另外,在《意见评论集》(Scriptum super Sententiis, lib. 2 d. 6 q. 1 a. 3 ad 3; lib. 2 d. 13 q. 1 a. 3 co.)中,托马斯谈到了光的反射(reflexio radiorum solis)。Reflexio radiorum solis字面意思是太阳光波的返回。即是说,reflecto还不能单独用来表达光的反射,而是像自我认知一样,需借助其他的词,经过转义才能表达光反射。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新时代(即近代)。这也表明,Reflexion并非黑格尔(参见:E3, § 112, Zusatz, TWA 8, S. 232; 1813, S. 13.)或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最初是个光学术语。
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intellectus(智力)的基本特征就被规定为反思:思维能够返回自身,对自身进行思维。中世纪晚期哲学家们对intellectus 日益增多的讨论也都是从这个基本特征出发的(参阅:Kobusch, S. 285ff.)。
新时代,该词的意思直接就是反思,而不再需要通过其转义——思维返回到自身——来表达自我认知这层意思了。笛卡尔将该词的原始义和各种转义广泛地运用于物理学、光学、生理学和哲学领域。不过,自笛卡尔始,该词也慢慢地只是作为一般的思维词汇来使用了,而不必非得是那种具有自身指向性的思维活动,或回到之前已思考过的事物,以便对其进行一种事后的“后思”(nachdenken),也就是说,该词原来具有的那种自身指涉性或事后性慢慢被遗忘了,至少不会被特别注意或提起。到了德国观念论这里,尤其是在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里,反思与思辨(即智性直观)之间的关系则是哲学争论的核心,并且是评判一个哲学体系成败与否的关键。
二、Reflexion的多重意义在黑格尔哲学中的相互关联
在《耶拿体系草案I》(1803/04)中的自然哲学部分,黑格尔将作为“绝对的物质”即“以太”(Äther)的绝对者规定为“显现着的本质”——光。光作为抽象的、肯定性的统一性将自身对设为月亮和彗星,而地球则被设定的对立面(月亮与彗星)的统一;光本质从太阳到地球的映现运动,即是光从无限的运动中返回到自身的过程(参阅:Jenaer Systementwürfe I, S. 3ff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黑格尔一开始就把绝对者把握成“绝对的思维”,自然也不过是 “与自身相关联的绝对精神”(Jenaer Systementwürfe II, S. 191)。从自然到精神的运动,乃是思维或精神返回到自身的运动:“在精神中,绝对简单的以太穿过地球的无限性而回到了自身。”(Jenaer Systementwürfe I, S. 183; GW 6, S. 265) 绝对者既是思维者,同时亦是显现者和返回者,Reflexion的三重含义——返回、反映、反思——从体系筹划的一开始就被黑格尔置于内在的必然关联中。
在《本质逻辑学》第一部分第一章“显现”(Schein)中,黑格尔对这三重意思及其关联予以了明确的揭示。“本质是Reflexion”(1813, S. 7),这句话首先是说,本质是反思,因为本质不过是我们一般的、两分的反思模式所直接预设或拿来的东西:我们习惯性地预设了各种存在背后的本质,而把存在视为本质的显现。因而,Reflexion这里也是显现/映现的意思。但这种本质不过是一个对反思来说直接而现成的“存在”,故本质自身也可以是其他存在者的“显现”,存在、本质与“显现”于是就成了一个东西。而存在向本质的发展,不过是存在回到了自身,或说是本质回到了自身,存在作为本质的显现,不过是本质在自身中的显现而已。本质运动作为一种在他物中的显现或映现活动,实则是一种在自身中的显现活动,这样,作为显现活动的本质运动无非是一种返回到自身的活动,而无论是作为显现还是作为返回运动的本质,都不过是思维自身的活动。本质本来是对存在的否定,但通过这里所述的本质运动,本质也否定了自己对存在的否定,即它也否定了自己,本质运动于是就被揭明为一种指向自身的否定性运动——绝对否定性。通过这种绝对否定性,我们才达到了正确的本质及显现之概念。正是基于Reflexion概念的多义性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我们才把黑格尔的理念称为返回者、显现者和自我认知者,一言以蔽之,绝对者即das Reflektierende。
三、本质-显现-现实性作为理念运动的模式
理念运动作为返回运动,是黑格尔始终未变的观点,在学界亦无争议。争议在于:第一,以本质-显现之模式来解释整个理念运动的合适性;其二,黑格尔明确将反思与思辨对立起来,因而,不能把反思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原则。
第一个反对要点在于,本质是逻辑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其最高阶段是概念,因而理念运动必须被理解为概念运动(该反对是Klaus Vieweg向笔者提出的)。首先,按此逻辑,理念运动应该被理解为精神运动,而不是概念运动,因为《精神哲学》才是最高阶段。其次,无论早期还是成熟时期的黑格尔都常常将绝对者或精神称为本质或绝对的本质,尽管他另一方面又将本质设定为逻辑学的第二阶段,并批判了以柏拉图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本质观以及宗教中的本质观。实际上,无论是存在、本质还是概念,抑或精神,等等,在黑格尔那里都具有广、狭义之分。当黑格尔说,理念在在绝对精神阶段达到了自己真正的存在时,实现了自己真正的本质或概念时,我们显然不能狭义地来理解这几个概念。无论我们用什么来称呼绝对者,或以何者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开端,绝对者一开始都只是一种抽象的、无规定的普遍性。因而黑格尔说,绝对者作为上帝或本质,最初也只是一个“抽象物”(Abstraktum)(1993, S. 229),“一个抽象的名称”(1993, S. 266)。即使我们把绝对者称为概念,这个概念最初也只是一种空洞的概念,并不具有实在哲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所代表的那种实在性。真正的概念是概念与实在性(自然和精神)的统一,即绝对精神作为“概念的概念”。黑格尔说,“自然和精神主要是展示绝对理念之此在的不同方式” (1816, S. 284);自然和精神是“永恒本质”的两种显现方式(参阅:E3, § 574-577)。只有通过显现,在逻辑学阶段还只是作为“纯粹本质”的理念,在实在哲学阶段才达到了其真正的本质即现实性;逻辑学表达的只是理念的概念,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即那种与理念相匹配的“恰当概念”或“概念的概念”,在绝对精神那里才完满达到。传统本质观和宗教中的上帝本质观,其不足在于:或立于两分的观点之上,或是一种不能把握各运动环节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的表象(参阅:E3, § 564-571)。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概念来称呼绝对者及其运动,而只在于无论我们怎么称呼绝对者,都必须基于那种否定性的反身关系来理解绝对者及其运动。当黑格尔把绝对者称为本质,将其运动称为显现时,他显然是站在《本质逻辑学》里所阐明的那种以绝对否定性为基础的本质-显现-现实性之运动模式/结构之上的。
四、思辨与作为思维活动的Reflexion
第二个反对的不足在于,首先它把多义的Reflexion只理解为思维活动,其次,进而将作为思维活动的Reflexion只理解为两分的观点。
众所周知,作为思维活动,Reflexion在黑格尔指的首先就是抽象的两分观点。这种两分的观点,黑格尔在其哲学生涯的一开始就加以了特别的关注和批评。早期黑格尔专注于宗教领域并将宗教分为客观的与主观的宗教。客观宗教导致的分裂在于,通过理性(或知性)、外部权威(教士或《圣经》)而来的关于上帝的知识不能使我们的生活与上帝统一,因为这种知识不能使我们信仰上帝。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主观宗教里才出现的真正统一是我们通过情感、爱和信仰而达到的。在谈到两分观点的时候,早期的黑格尔一般用的是知性(Verstand)一词。明确将Reflexion界定为两分的思维是黑格尔在《宗教与爱的草稿》(Entwürfe über Religion und Liebe (1797/1798))中做出的:“[……] 在发展中,反思总是制造越来越多的对立的东西 [……]”(TWA 1, S. 246)早期的黑格尔虽然将Reflexion与知性等同起并批之为两分的思维,但还没有将它与思辨(Spekulation)对设起来。正如在早期的德国观念论那里,知性、反思、理性或思辨,在早期的黑格尔这里也是不加区分的,相互可以替换,是一种与爱和信仰对立的、达不到真正统一的有限认知能力:“神迹的捍卫者们并非将他们的事情与自立的、独立地单从自身为自己设定目的的东西编织在一起,而是与理性的武器,与这种从外面来设定目的的东西编织在一起[……]”(TWA 1, S. 215f)爱则“排除了一切对设,它不是知性 [……] 不是那种毕竟将它的规定活动与被规定者对设起来的理性[……]”(TWA 1, S. 246) 诚如Klaus Düsing所言,“早先 [......] 反思之两分是与生活的统一相对立,而思辨道德者的思辨本质上并没有同反思相区别”(Düsing, 1969, S. 116)。在早期的黑格尔那里,绝对者并非通过认知来达到的。这个观点,后来的黑格尔必须要加以抛弃,因为绝对者必须是可以被认知的,否则它就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
在《费谢体系差异》(Differenzschrift)中,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将反思与思辨对设了起来,并自此开始,将哲学史上几乎所有之前的哲学(并非只是康德、费希特、雅可比和谢林的哲学)都称为一种未能摆脱两分观点的“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 这也说明,即使作为两分观点,Reflexion的含义或表现形式在黑格尔那里也是不尽相同的,又是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它首先指的是一种直接性意识,比如现象学里的感性确定性和百科全书中思维对待客观性的第一种态度,对应的是理念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状态。这种意识直接将某物采取为真者,而毫不怀疑,不加反思,它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无反思的反思,即黑格尔所说的“信仰”或“单纯的知性观点”(E3, § 26f, TWA 1, S. 93f)。以康德和英国经验论为代表的思维对待客观性的第二种态度,显然是更为深刻的、批判性的观点,而不是直接性意识或信仰。第三种态度是基于智性直观之上的对真理的直接确信,因而它在黑格尔看来正如第一种态度一样,是一种信仰,尽管与前者不同,后者是立于感性的确信之上的。尽管这三种态度相互间有着显著的区别,但黑格尔统称之为“外在的”、“知性的”、“抽象的”、“孤立的”或“有限的”的反思,正如他在《费谢体系差异》、《知识与信仰》(Wissen und Glauben)中将当时的哲学(康德、费希特、雅可比)统称为“反思哲学”一样。另外,如果我们将反思等同于知性,那么,看似矛盾的是,知性在现象学里是后于感性确定性与知觉的,它是更高的意识形态,如此一来,感性确定性与知觉以及百科全书里的第一种态度,似乎不能被归属在反思概念之下。我们与其去指责黑格尔在用词上的不严谨性,不如说他的很多术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动态的意义流变和相互的纠缠中而为黑格尔辩护。在反思概念之下,黑格尔的主要目的是去批判那些未能在对立中去把握统一的所有的思维或意识形态。正是出于这种被黑格尔诊断为时代弊病的两分,才有了哲学上统一的需要——思辨。
思辨的核心之处,黑格尔在Differenzschrift中已经清楚地做出了规定:为了扬弃对设,理性一方面消灭对立面,另方面在统一中又保存了对立面(Differenzschrift, GW 4, S. 17f)。思辨思维的特征,简言之,就是要“在对设中去把握诸规定性的统一”(E3, § 82),它达成的是那种关于“处于统一中的对立面的知识”(GW 10, 2, S. 831)。“思辨思维的本性惟独在于在统一中对诸对立环节的把握。”(1812, S. 95f)。思辨也即作为双重否定的辩证法。在1816年的《概念逻辑学》中,黑格尔对辩证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参见:1816, S. 283-306)。它是“认识着自身的概念,是将自身作为绝对者、既作为主体性的东西,也作为客体性的东西,也即将其作为对象来拥有的概念”(1816, S. 286),是“规定着自身、自我实现的[概念之]运动”(1816, S. 286)。辩证法是理念及其运动,也是理念实现自我认知的方法。认知与被认知者,认知的方法,是同一个理念。辩证根源于绝对者作为思维自身所蕴含的源分裂(Ur-teil)——矛盾或对立,这种源分裂首先表现为那种外部的相互对立与否定关系;从柏拉图到康德,他们的辩证法就属于这种简单的辩证法,即黑格尔所谓的“外在反思的辩证法”(1832, S. 93)。黑格尔之前的传统辩证法,归纳起来,就不外乎是黑格尔在百科全书里所说的逻辑者的第一、第二个方面,即简单知性的与否定理性的辩证法。矛盾或对立是以前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自己的思辨的辩证法的共同基础。两者的分水岭在于:前者从矛盾导向无,而后来则在对立中建立起肯定的东西来(参阅:1816, S. 294ff)。
当然,作为思维活动的Reflexion,在黑格尔那里,也并非只是指两分观点。在那封被经常被引用的黑格尔于1800年致谢林的信中,黑格尔说要把青年时的理想转变成“Reflexion形式”(Reflexionsform)。早就对两分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的黑格尔这里用“Reflexion形式”指的绝非两分的体系(即黑格尔日后一再批判的“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而是指他在耶拿时期(1801-1807)就开始筹划的那种真正的哲学思辨的体系(philosophiae speculativae systema)(1967, S. 54.)。在《费谢体系差异》中,黑格尔虽一方面明确将反思与思辨对立,但另方面他又将Reflexion称之为哲学的一般工具,明确地区分了思辨或理性意义上的Reflexion与知性意义上的Reflexion,并认为,知性、理性、Reflexion可以超出两分的思维模式而将自身提升到真正思辨的高度(参见:Differenzschrift, S. 15ff.)。现象学里的外在反思作为外在观察者,是已然完成了的哲学科学的观点,即思辨的观点;在从逻辑、自然到精神的整个理念运动中,它也始终是具名或匿名地在场的,一直参与、执行或追溯、回忆着理念的运动,并最终被揭明为精神或理念自身的思维运动。于是,外在反思,作为外在推动力,即是理念运动的内在推动力,作为主体,它就是“观察着的概念”(1816, S. 287),作为方法,它就是“事物自身的过程”(1832, GW 21, S. 38)。也因此,我们的外在反思在逻辑运动的最后即在绝对理念那里才成了多余的,因为“理念从此是自己的对象了”(E3, § 236, Zusatz, TWA 8, S. 388)。“我们的反思成了可以被概念自己的反思所替换的东西”。(Jaeschke, 1978, S. 111)
就现象学里的“绝对知识”或百科全书里的“绝对精神”只是在最后才能被达到而言,哲学史上、黑格尔之前(甚至之后)的所有哲学形态作为百科全书里思维对待客观性的不同态度,现象学里“哲学科学的观点”之前的所有意识发展阶段,百科全书中“绝对精神”之前的所有理念运动,简言之,即逻辑者的第一与第二个方面,作为绝对思维的不同显现,都要被标识为某种反思即对立的东西。理念的整个运动,正是不断地历经着这样的“否定性之痛”的(E3, § 569, TWA 10, S. 376)。因而,即便我们把黑格尔的Reflexion概念片面地理解为两分对立的观点,那么,理念运动的特征百分之九十九却正是由Reflexion来刻画的。而思辨则是不断地超越又重新陷入对立中的、因而不断地否定自身、自我提升的过程。这个自我提升,黑格尔又称之为教育/形成(Bildung)之过程(参见:TWA 1, S. 246; Differenzschrift, GW 4, S. 13ff),而教育也并非仅仅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教、养之过程,它指的更是理念或绝对者的自我教育和构成的过程。这个自我提升、教育与构成过程不仅是现象学的主题,同时也是整个理念运动所表达的主题。因而,与费希特、谢林在智性直观即思辨上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的直接性不同,黑格尔的思辨绝非某种直接性的自我确信,而是一种经由自身中介的、自我否定的、自身与自身关联的(selbstbezüglich)即反身性的(reflexiv)自我认知。哲学史上和理念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不过是思维本身即绝对者的不同显现形式而已,而通过在自身中的显现,理念返回到自身,实现了自己真正的本质、概念或存在,也即达到了对自身的认知。
参考文献
Hegel, G. W. F.,
TWA: Theorie-Werkausgabe, Werke in 20 Bänden, Frankfurt am Main, 1969ff.
GW: Gesammelte Wer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68ff.
E3: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 hrsg. von Friedhelm Nicolin und Otto Pöggele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1. = GW 20.
1812: Wissenschaft der Logik: Das Sein (1812), neu hrsg. von Hans-Jörgen Gawohll,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Hogemann und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9. = GW 11.
1813: Wissenschaft der Logik: Die Lehre vom Wesen (1813), neu hrsg. von Hans-Jürgen Gawoll,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2; = GW 11.
1816: Die Lehre vom Begriff (1816), hrsg. von Hans-Jürgen Gawohll,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Hogeman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3; = GW 12.
1832: Wissenschaft der Logik: Die Lehre vom Sein (1832), neu hrsg. von Hans-Jürgen Gewoll,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Hogemann und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8; = GW 21.
Differenzschrift: 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in: Jenaer Kritische Schriften (I): 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Rezensionen aus der Erlanger Literatur-Zeitung; Maximen des Journals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neu hrsg. von Hans Brockard und Hartmut Buchne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9; = GW 4, S. 1-92.
Jenaer Systementwürfe I: Das System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Fragmente aus Vorlesungsmanuskripten zur Philosophie der Natur und des Geistes, neu hrsg. von Klaus Düsing und Heinz Kommerl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6; = GW 6.
Jenaer Systementwürfe II: Logik, Metaphysik, Naturphilosophie, neu hrsg. von Rolf-Peter Horstman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2; = GW 7.
1993: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Der Begriff der Religion, neu hrsg. von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52: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d. I: 1785 – 1812, hrsg.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67:„Dokumente zu Hegels Jenaer Dozententätigkeit (1801 – 1807)“, hrsg. von Heinz Kimmerle, in: Hegel-Studien, Bd. 4, Bonn: Bouvier Verlag,.
Augustinus, 1991, De vera religione (Über die wahre Religion), 39. 72, übers. von Wilhelm Thimme,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
Thomas von Aquin, 2006, Summe gegen die Heiden, Bd. IV, hrsg. und übers. von Markus H. Wörn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üsing, Klaus, 1969, „Spekulation und Reflexion: Zur Zusammenarbeit Schellings und Hegels in Jena“, in: Hegel-Studien, Bd. 5, Bonn: Bouvier.
Jaeschke,Walter, 1978, „Äußerliche Reflexion und immanente Reflexion. Eine Skizze der systematischen Geschichte des Reflexionsbegriffs in Hegels Logik-Entwürfen“, in: Hegel-Studien, Bd. 13, Bonn.
Kobusch, Theo, Die Philosophie des Hoch- und Spätmittelalters, München: C. H. Beck, 2011.
Historischen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Joachim Ritter und Karlfried Gründer, Bd. 8: R-Sc, Basel: Schwabe, 1992.
[abstract]: the threefold meaning of the reflection in the history — return, reflex or appear, selfthink — and their immanent, inevitable relation to to each other in Hegel’s system, expound the connotation of Hegel’s idea-movement: what Hegel's system describes, ist exactly the absolute’s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itself, appearing in itself, and this process is meanwhile a process of it’s self- cognize. Hitherto, this intrinsic relationship and its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the Hegelian system has not been taken seriously, sufficient. Instead, we follow Hegel one-sided, take Reflexion simply as a bisect standpoint opposed to speculation. In fact, Hegel'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s an external observer is itself a process of self-promotion, selfeducation or selfformation, and parallel to the movement of spirit or idea, and the speculation which is profoundly redefined by Hegel, is by no means some kind of Fichte and Schelling’s intellectual intuition - a direct self-consciousness or confidence in the absolute,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of speculation is precisely selfthinking based on absolute’s negative self-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