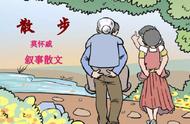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如今的闰土,已然与记忆中的闰土成了两样。曾经带着银项圈的少年,即使是夜里守瓜也是快乐的,如今满脸沧桑,疲态尽显。

与记忆中的面目大改相一致的,是一颗少年纯粹热烈的心被摧残殆尽。
在鲁迅的心中,他与闰土应当仍然如同少年时一般亲密无间,因而当他见到这个面目大改的闰土之时,仍然一句“闰土哥”脱口而出,然而闰土开头喊他的却是一声“老爷”,这不禁让他打了一个寒噤。
横亘在二人之间的,除了未曾联系的岁月之外,还有二人精神上的差距。幼年闰土将鲁迅视作自己的玩伴,成年闰土却将其视为与自己有着阶级差距的“老爷”,即使鲁迅的母亲表示可以直接将鲁迅称为“迅哥儿”,得到的回复也是“这成何体统”。

体统是什么?是当时束缚着每一个贫苦阶层内心的一道枷锁,它让人们在痛苦的挣扎之中认清现实,接受命运,并且承认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
这对于当时受过新式教育主张破除一切旧的礼教的“我”而言,是何等讽刺的景象。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封建思想仍存于每个人的心中。
这种无力与挫折,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透露在《故乡》的字里行间。
然而,这段悲伤的故事,放在当下,放在如今的时代,仍然蕴含着人生哲理。

或许我们最为感触的是贫苦的生活以及礼教的枷锁将鲁迅折磨成“我”无法接受颇为心痛的形象,但实际上,我们能从这篇文章中看出的远不止如此。
成年闰土,是鲁迅从母亲的口中听到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除了鲁迅想着记忆中的闰土之外,闰土也从来没有忘记过曾经为时一月的玩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