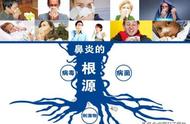在东晋世家大族谢家,有一日谢太傅将儿女们召集在一起商讨文章的义理,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于是谢太傅便问众人:“天上的白雪像什么啊?”
谢朗率先回答:“撒盐空中差可拟。”翻译过来就是:“像空中撒盐差不多可以相比较”。
谢太傅点了点头,看向了一旁的谢道韫。
只见谢道韫不慌不忙地说道:“未若柳絮因风起。”
两者相比,高下立判,前者只是从外观上描绘出了雪的状态,雪刚下时呈现出的颗粒状态,这个时候的雪被称为“霰”。
呈现出颗粒状的雪在下落的时候速度较快,并且在落地之后会弹跳,其实与盐十分相符,但终究停留在表面,如同《咏雪》中的前半阙“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未免落了下乘。

但谢道韫将白雪比作是乘风而起的柳絮,不但写出了大雪纷纷的感觉,更是蕴含了希望冬天快点过去,春天能够来临的期望。
将自身情感融进了诗句中,使得整个句子除了形象外,更加丰富起来。也就如同《咏雪》的下半阙,“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都不见”使得语句在感情的加持下得到了升华。
同样是描写雪,语言也同样简练,但是否融入了感情却是区分佳作的关键原因,而这样的简洁描写不仅仅出现在对雪的描述中。
例如宋代邵康节所作的《山村咏怀》。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在《乐府诗集》也有《江南》一首: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看似都是简单的描写,却总是带有一种形象生动之感,诗词所描绘的场景更是直接呈现在观众眼前。
而反观近代,著名小说家余华所写的《活着》同样如此,用语用词简洁明了,但似乎每一个语句都显得苍白,每一声叹息都显得无力。
尽管余华自己曾经调侃道自己之所以语言简练是因为自己认识的字少,但那自然是玩笑话。
简答的文字未必不能传达深邃的力量,胡适先生当年极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就是因为其繁琐复杂,依靠咬文嚼字辞藻堆积固然可以渲染感情,但三两句简单的描写同样可以表述其意。
被人称为“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自然也写得出对仗工整的佳作,但在作诗时,书生们嘲讽他的粗鄙,误认为他是没有文化的乡野村夫,而郑板桥又何尝不是在回击他们。
既然你们认为我没有学识,那我就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写出你们咬文嚼字也赶超不上的作品,如此傲然的性格,也不愧为“扬州八怪。”

如今,很多人推崇梵高的画作,正是他将个人情感画进了作品里,人们可以通过他大胆地用色直观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烈。
而这首《咏雪》同样如此,也许会有人觉得一片两片的描写太过俗套,可当你抓心挠肝,搜肠刮肚后却发现,再没有任何一句话,能更直白地表明下雪的景象了。
过于华丽繁琐的描写并不一定是好的,齐白石在画虾的时候都会特意留下一点空白,反而更能体现虾的通透之感,诗词同样如此。
有时候,简单,才是最好的。
参考文献《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人民网
《浅谈郑板桥笔下的“萧萧竹声”》中华网
《郑板桥年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板桥集》岳麓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