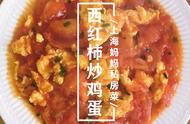来源:维基百科
我们可以想象经验主义(empiricism)是一个复杂过头的形式系统,各式各样的本轮循环(历史上用于解释天体运动的复杂数学模型)充斥其中,辅以各种推理规则以求获得科学真理,不一而足。我们甚至可以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关于科学主要是关于证伪的观念中看到将科学形式化的萌芽(尽管托马斯·库恩(Kuhn)关于科学是一系列范式转移的反论似乎更难形式化)。再次强调,至少可以设想科学可被视为一个抽象机器,也许这台机器的唯一目标甚至相当简单,就是“推翻假设”。
尽管在将科学概念化为形式系统方面已有一点现代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及这个问题所值得的深度,它对不同科学领域影响是什么也几乎没有探索(比如:不会问“不完备性会在哪里出现?”)。
事实上,由于科学本身对数学的依赖,不完备性可能不可避免地会渗入科学。这正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尽管他以穷极一生追求“万物理论”而闻名,但在生命晚期,霍金得出结论:这样一个理论是不可能的。他的推理是:科学对数学的依赖太深,因此不确定性悄然而至——科学从数学那里“继承”了悖论。
所有这些思想都有着悠久的知识谱系。关于物理学是否可以建立在一组公理基础之上的问题,是希尔伯特(Hilbert)在1900年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之一。他写道:
对几何基础的研究引发了这个问题:用几何研究同样的方式,通过公理来处理物理科学,在其中数学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希尔伯特来说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事实上,希尔伯特会有兴趣知道,我们已经知道物理学似乎包含着不可判定的性质。这些性质有很多,但同样都很少被讨论。例如,2015 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光谱间隙的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 of the spectral gap)的论文,指出一个重要的物理量——物质基态与初始激发态之间的能量差——在形式上是不可判定的。这也是由递归引发的(基本上,他们把关于谱隙的问题编码成谱隙)。
至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可以说科学是不完备的!至少,我们知道有一些物理属性无法(以严格或系统的方式)真正被发现。当然,科学是不完备的结论也并非那么理所当然。不过如果这个结论正确的话,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意识这个难题如此之难。

我当然不是第一个指出意识和自指性存在奇怪之处的人。但我实际上认为,很多相关工作并没有直接触及科学的不完备性——人们通常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在某处被详细阐述,但随后却难以找到明确的来源。
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皇帝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认为,人类可以理解计算机无法理解的不可判定语句,因此人脑不是个计算机。然而,人脑是不是计算机并不能真正告诉我们科学是否完备,也不能告诉我们理解意识的困难是否来自科学的不完备性。
在柯林·麦金(Colin McGinn)的《神秘的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一书中,他主张“神秘主义”立场,即意识——你从书名就猜得到——必然是个谜。不过,麦金认为,意识在原则上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解决的,只是人类本身缺乏智慧(就像狗缺乏理解广义相对论的智慧一样)。比方说,对于超级智能 AI 来说,意识就不是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所著的极为经典的《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ödel, Escher, Bach)——一本关于递归和心智的妙趣横生的书。事实上,我发现人们常常认为《哥德尔、埃舍尔、巴赫》的中心假说是关于科学的不完备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是没有明说。如果你读了后续的《我是个怪圈》,就会明白侯世达想说的是,意识只是大脑中的符号递归。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理论,因为即使是游戏《天际》中的 NPC 角色也可能拥有基本的符号递归,而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拥有意识(膝盖中箭也并不会真正伤害到他们)。无论如何,科学不完备性的观点与符号递归是意识之根的观点彼此是正交的——这里所主张的并不是“意识产生于递归”,而是在科学体系下“意识理论本身具有递归性”。
关于科学不完备性的最早期原型陈述之一,我发现实际上是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那本几乎被遗忘的心理学著作《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老实说,他的论点并不是很好。基本上,他认为你无法理解一个自然现象,除非拥有比它复杂得多的系统,而我们不具备足够的神经复杂性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大脑(这个观点似乎立即被诸如“那么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天气是如何运作的”等反例所削弱)。
但这些都没有直接论证科学的不完备性,这就是我在《世界背后的世界:意识、自由意志和科学的局限性》(The World Behind the World: Consciousness, Free Will, and the Limits of Science)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的原因。为了尽可能直接地阐述,我在书中将科学不完备性定义为:
意识理论就像是用科学语言写成的哥德尔句子。

我公开承认并不存在直接证据证明这一论点。但却存在间接证据,以及通向哲学证明的可行途径。
例如,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探讨传统上所谓的“心身问题”,都会陷入悖论。一方面,一旦我们用科学世界观对自己进行编码,就会意识到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们的意识)。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在《本然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一书中对此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想象一下,科学世界观实际上是一张地图(大概是宇宙地图)。它可能是完整和连贯的,宛如公理般地一致。但地图上明显缺少了一条信息:“你在这里”的标志。而这一额外的信息将你——观察者——与地图本身联系在一起,但地图本身并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