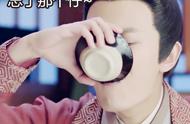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在很远很远的海上,那里水像最美丽的矢车菊那么蓝,像水晶那么清澈,非常非常深,说实在的,深得没法用锚链来测量它的深度。就算把许多许多教堂的尖塔一个接一个叠起来,也不能从下面的海底达到上头的海面……”
不知有多少人在小时候听过或读过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也译作《小美人鱼》),被故事中小美人鱼的纯真、勇气和善良深深打动。然而日前,这则全球知名的童话故事在中文互联网上意外引爆了“应不应该给孩子读”的激烈讨论。
3月24日,微博网友“轻成一只飞燕”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女儿讲过《海的女儿》这种“经典童话”,批评男人(即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写的童话毫无逻辑可言:“就为了一个只看过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资源(美丽的长发)、自我的阉割(无法说话)和终身痛苦的代价(直立行走如刀割),换一个所谓的爱情……矮化海洋女性物种,跪舔人类男性。”她的结论是,所有有着幸福快乐结局的王子公主式童话都不适合讲给女孩听,因为女孩不能只是“年轻美丽柔善可欺”,嫁人亦非女孩人生的唯一选择。

截至29日下午,这条微博的转发量已近万,引起了包括数位微博大V在内的网友的激烈辩论。在发出上述微博次日,“轻成一只飞燕”站出来澄清说,她反对的不是安徒生的原作,而是国内只有两三页纸的删改版《海的女儿》,称反对的原因是抵制刻板审美对孩子的无意识影响。针对网友对其“阉割孩子的阅读权限”的批评,她表示,家长有责任为孩子筛选童话故事,“这就是低幼儿童的局限性,她无法自己选择,家长给她看什么她就能看到什么,你心疼她也不能替代我抚养她,她再可怜也只能等着自己长大。”
包括这位网友在内的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童话就是“给孩子看的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安徒生本人就在发表收录《海的女儿》的故事集时说过,“其他童话比这一篇更是儿童故事,而这一篇含义更深,只有大人能够理解;但是我相信,孩子光是看故事也会喜欢它的:故事情节本身就足以把孩子们吸引住。”
追溯童话的历史,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曾引用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冯·德·莱恩的研究指出,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和埃及就已经出现了童话故事,公元前2000年在印度和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童话故事,接着有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童话故事。卡尔维诺发现,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将童话视作“儿童文学”,然而直到19世纪,童话更多是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下的奇幻故事存在的,并没有读者/听众年龄的划分。比如在1815年首次出版的格林童话故事集《献给孩子和家庭的童话》,就是由格林兄弟整理、记录并编撰民俗传统中的诗篇与故事而成。与其说这些故事是“童话”,不如称之为“民间口述”更为恰当。
所以,童话不仅是给孩子看的,更是给成人看的。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随着智识和阅历的积累,我们对同一个故事文本亦逐渐有了更多元、更丰富、更深层的理解,这种理解决定了童话的意义阐释,乃至孩子的阅读选择。
必须承认的是,在多元化的文学意义阐释中,女性主义已然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主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即通过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权政治话语进行文本分析——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Mary Ellmann、Kate Millett和Germaine Greer等女性知识分子推出著述,动摇了人们对以男性为中心、贬低压制女性形象的文学的无条件接受。而在反性*扰运动席卷全球、再次唤起人们对性别政治普遍自觉的当下,有强烈平权意识的妈妈们对“经典童话”心存警惕也顺理成章。尽管如此,在女性主义阐释逐渐变成文学批评的“新常态”,乃至成为决定文学价值的统摄性力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它背后的危险。
安徒生“仇女”?《海的女儿》争议史
童话是一个口口相传的、在叙述者和听众之间被不断加工、改造、复述、传播的产物。在卡尔维诺看来,所有的童话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成为了某种人类思想经验和社会现实的抽象概括,“决定了世间男女的命运,尤其是对于生命中受命运支配的那部分。”河合隼雄结合荣格心理学理论指出,童话、寓言与神话充满了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而这些故事传播的重要心理要素,就是传达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型性(archetypal)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史研究者常常会在全球各地发现一些核心内容相似的童话作品。

在男权社会中,童话是否隐含着性别规训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以“睡美人”为例,在格林童话故事集和法国童话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鹅妈妈的故事》中,都有这个故事。两则故事中都有一个关键情节,在公主降生的庆祝宴会上,几位仙女分别赠给公主一样礼物。在格林童话中,仙女们赠送的分别是德性、美貌和财富;在佩罗的版本中,仙女们赠送的是贤良、端庄、能歌善舞、精通乐器等技能。两个故事都强调了“世上的人追求的东西,一个不少地赠送给了公主”,河合隼雄指出,虽然格林兄弟和佩罗选择的仙女馈赠各有异同,但它们都是反映女性特征的、值得女性追求的品质。

作为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经典童话故事,《海的女儿》一直以来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典型案例——小美人鱼为了王子牺牲自己的声音、身体乃至生命,这被广泛认为是塑造了一个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文化刻板印象。为了化身成人获得不灭的灵魂,小美人鱼找到海女巫请求帮助,海女巫提出了一个恐怖的建议:
“我要给你煮一服药,你必须带着它在明天日出前游上陆地,坐在海岸上把它喝下去。喝了以后你的尾巴便会消失,变成人类称为腿的东西,那时你将感到剧痛,就像一把剑在插进你的身体。但是所有见到你的人都会说你是他们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小人。你的动作将依旧像游水一样优美,没有一个舞蹈家的步子能那么轻盈;但是每走一步你都会感到像踩在尖刀上。”
另外,海女巫提出小美人鱼需要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但是我也必须得到报酬,而且我要的不是无所谓的东西。你有胜过海底任何一个的最甜美的嗓子,而且你自信能用它迷住王子,你却必须把这嗓子给我;我要你所拥有的最好东西作为我给你的药的代价。”
许多学者在研究安徒生童话时聚焦了这一关键情节。在《小美人鱼: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女性身份认同》(The Little Mermaid: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Feminine Identification)一书中,Robert W. Meyers认为用嗓音交换魔药、用忍受行走在刀尖上的痛苦来换取成为人类的权利,象征着女性“放弃了言说和被理解的权力、丧失创造性以及被阉割”。博客网站Medium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也指出了嗓音背后的“女性意见”隐喻,认为《海的女儿》实质上是告诉女性应该为了男人或为了融入社会而放弃言说的自由。作者Kidd Dark认为,尽管故事的核心思想是善良与救赎之间的关系,但这一主旨无法掩盖故事本身的“仇女”论调和“女性低等”的落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