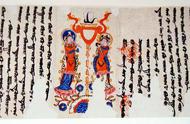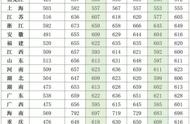1937年9月18日在上海出版的《七月》周刊第二期
胡风在1935年评论黄源主编的《译文》杂志时指出:“一本杂志也是一篇创作,那里面的文章就是题材”。如果把《七月》杂志看成是胡风创作的一篇文章的话,可以说,“鲁迅”就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胡风作为鲁迅的精神衣钵传人,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大力提倡鲁迅的启蒙精神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试图通过《七月》杂志来“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他不仅团结一大批进步的青年作家和木刻家投身于抗战的宣传之中,而且也以富有理论远见的批评文章指导青年作家在鲁迅精神旗帜的引领下,为追求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周刊创刊于上海,刊名之所以取名为“七月”,是为了纪念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欢迎这个全面抗战的发动期底到来”,另外,“七月”两字采用鲁迅的手迹墨宝,则是为了表达对鲁迅的纪念。可以说,《七月》杂志由此把宣传抗日战争与纪念鲁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弘扬鲁迅精神,而且也以鲁迅精神来指导抗战宣传工作。
《七月》周刊在上海共出版了三期,这三期所刊登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受到鲁迅影响的进步作家,如胡风、萧军、萧红、曹白、端木蕻良、艾青、刘白羽、丽尼等,另外,还刊登了一些美术作品,如李桦创作的木刻《被枷锁着的中国怒吼了》和《旗手》、野夫创作的木刻《保卫我们的城池》、陈烟桥创作的漫画《我么也要去*日本强盗,给我们枪呵!》。总的来说,这些文章、诗歌和美术作品的主题都是宣传抗战的。

《七月》周刊第二期上的陈烟桥漫画:给我们枪呵!
《七月》周刊第二期刊登了胡风的诗歌《给怯懦者》,这首诗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呼吁在抗战时期怯懦的人们拿起武器反抗敌人。
《七月》周刊第三期还刊登了鲁迅之子周海婴手写的儿歌《打日本》。周海婴当时只有8岁,杂志在刊登这首儿歌时采用了周海婴稚拙的手迹,更形象地表达出作为鲁迅之子的周海婴反抗日寇的精神,很好地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标志着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因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形势日益复杂多变,9月11日胡风在上海创办的《七月》周刊,至9月25日出版第3期后就被迫停刊了。
与此同时,胡风从上海撤离去往武汉,10月1日到达汉口,他的好友熊孑民亲自去码头,将胡风接到汉润里42号楼上安顿住下了。梅志和孩子此时还暂住在湖北蕲春的胡风老家。胡风在去武汉途中的轮船上经过老家蕲春时,虽然是那么想念结婚以来首次别离的年轻妻子,不知她和孩子过得怎样,但因要在武汉继续编辑出版《七月》等工作繁重又紧迫,所以,他忍住没有下船回家而只在想念中口占小诗一首:“午夜凭栏望,乡园一梦横。欲呼卿小子,云水了无声。”
五
汉口汉润里是由业主周五常(亦名周扶九)于1917年兴建的石库门里分(上海人称为里弄),他作为一个江西人在汉口经商致富后,为了润泽乡里,故将此新落成的里分命名为“汉润里”。1921年周五常在上海去世后,周五常的家人遂将汉口汉润里卖给了当时的湖北首富程拂澜。
汉口汉润里今位于武汉市南京路与黄石路之间,西至中山大道,北通文华里。里分内有纵横6条巷道,建筑格局是一栋一号,正门对正门,后门对后门,正门相对的是4.5米宽巷,后门相对的是3米窄巷,面临大街的100多米,则都是商铺。抗战时期的汉润里42号,经考证,应该就是汉润里主通道最后的那一栋,该房屋的现状与胡风笔记中的描述完全相符。
2015年3月22日,笔者陪同胡风的女儿张晓风教授,寻访找到了汉口汉润里42号,当年的42号就是现在的汉润里35号。1937年至1938年的门牌号码,是将汉润里临大街的商铺门面也编入了汉润里,主要是因为当时汉润里1—42号的产权,全都属于程拂澜与程子菊这叔侄俩的程家。1946年1月,武汉三镇的街道里巷重新编排了一次门牌号,汉润里的商铺门面此次则被编入了中山大道序列,所以,汉口汉润里的门牌号就只剩下了1—35号并沿用至今。

左起第三位是胡风的女儿张晓风教授,她与笔者(左二)等陪同人员在当年胡风主编《七月》半月刊的汉口汉润里42号(今35号)旧址合影留念

当年胡风主编《七月》半月刊的汉口汉润里42号(今35号)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