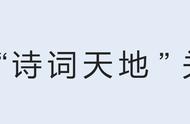一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人生是以一定的职业为载体的。二千多年前,古人就以士、农、工、商等来划分社会职业。在今天,我们常将社会职业概括为三百六十行。事实上,由于科技革命和体制创新等的持续推动,产业形态不断生长、裂变和细分,社会职业已远超这个数量。
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总体上,还是可以把职业类型粗分为为官、从商、治学等几大类。所谓人生之成功或辉煌,常常是指人们在从事这些职业时所取得的成功或实现的辉煌。
做了大官、赚了大钱常常被视为人生成功或辉煌的标志。人们认为,当官赚钱带来的好处是直接的、显著的,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按理,做成了大学问也应在成功之列,但由于治学不一定能直接带给人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在世俗的眼光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许多人对“金榜题名”者投以羡慕的目光,往往也是因为他们具有了升官发财的资格。作为职业选择,治学则是明显的冷门。
对此,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远在春秋时期,古贤人就深入讨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在与晋国名臣范宣子就何为“死而不朽”所做的对话中,认为“世䘵”或荣华富贵并不能构成人的“不朽”。
他认为,真正的不朽应当是立德、立功、立言,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对“三立”做了诠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简言之,它们分别指的是在弘道立德、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上做出的杰出成就。是否“不朽”,不由当事人自诩,也非他人对健在者的夸赞,而是后人对逝者的公正评价,是历史对一些人的“盖棺论定”。
此后,不少忠良贤达提出了类似的思想观点,例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王阳明的“人生第一等事”不在“登科获取功名”,而在读书“做圣贤”;清朝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
这些震古铄今的哲语箴言,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人生的意义,展现了一种忠于国家、服务社会、敬业向上的价值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和毕生追求。
人生,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的自然生命存在的全过程。但自然生命是有限的,对有限生命如何实现无限价值的超越性情怀,构成了历史上许多贤达之人对人生意义追求的重要方面。“三不朽”之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人生的含义。
它表明,人的生前身后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人生不仅体现自然生命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为社会影响的存续时间,或者说,一个人的存在,并不止于生前,也体现在身后,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对此,我们能从传统文化关于“死亡”问题的认识中获得较为深刻的领悟。今天人们认为没有区别的死亡二字在古人看来却是有很大差异的。古人认为人皆有两命,一为生命即物质肉体之命,一为性命即心灵思想精神之命。“性”为生加心字旁,这一造字结构形象体现了古人的深意。
“死”被看作是肉体生命的终结,而“亡”则意味着思想和精神的湮灭。老子《道德经》言:“死而不亡者寿”,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即所谓亡者忘也。“亡心”了,或者“心亡”了,才是完全死去了。
因此,人的寿命不在于肉体存活多久,而在于被世人记住时间的长短,那些对人类社会有立德、立功、立言贡献的人,虽然离开了人世,但却活在世人的心中,为后代所传颂和怀念,这些人虽死犹生,所以是长寿的。我们能看到,许多古贤人虽然已离世千百年,但在今天仍被热烈颂扬,其声名之盛大大超过了在世的名人。
正如当代诗人臧克家描述的那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纵观历史,许多人忍辱负重、披肝沥胆,其志就在于以卓尔不凡的建树增益于社会,“赢得生前身后名”。
广义的人生实际上包括三个阶段:工作阶段、退休阶段和身后阶段。如果以自然之身为形,以精神之身为神,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身后阶段是既无形更无神的。只有少数人,即使形已归去,“神”也依然长存。
要实现“三不朽”,赢得生前身后之名,必须付出特殊的努力。而就三阶段而言,大体上是工作阶段决定退休阶段,而生前决定身后。这意味着,对很多人而言,承担某种职业的工作阶段对人生建树起着决定性作用。
范恒山先生出席国务院新闻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