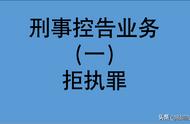(证据卷二十七p38 孙某供述)
二、从孙某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等,可知其不具备从事非吸犯罪的主观故意
(一)专业背景、从业经历等,依法可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犯罪主观故意的依据
根据《最高检座谈会纪要》[2]第9条的规定,“在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时,可以收集运用犯罪嫌疑人的......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此前任职单位或者其本人因从事同类行为受到处罚情况等证据。”
(二)孙某的教育背景及从业经历,可以印证其对隐蔽性强的金融犯罪,不具有识别能力
根据在案证据[3],结合会见时孙某的陈述[4],孙某系某市某大某某系05年的毕业生,一直到2015年,从事的均是互联网业务。进入涉案公司前,在宜某公司[5]互联网部门负责智能投顾基金,也属于互联网板块。
2018年3月,在猎头公司运作下,孙某入职金某公司,从大公司的经理,转到小公司任职较高级别的领导,是孙某当时的职业规划,也符合一般人的职场发展预期、人生发展规划。
而孙某入职前,也通过企查查了解涉案公司的情况,还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金某公司具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所要求的ICP营业许可证书,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等资质,公司先后荣获“杰出互联网金融创新者”“优秀p2p平台创新奖”“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透明度优秀企业奖”“201X年中国互联网安全之星”等众多荣誉[6]。
在如此多荣誉与政府背书的情况下,要求孙某认识到这样的公司可能涉嫌违法,显然是强人所难。”
据孙某陈述,他有宜某线上运营的经验,而涉案公司是线下起家,当时想找他发展线上业务。也就是通过互联网方式,扩大广告投放,但孙某刚入职就遇到了P2P行业“爆雷”潮。孙某入职当时,完全是想把自己之前在宜某的技术经验,应用到新的技术岗位[7]。
实际上,因孙某系从外围高薪挖角的技术人员,并非“信某系”内部成员,无法接触到公司的核心业务板块,短时间内两次被迫离职,均因与高层的意见不和。

(证据卷二十七p21 孙某供述)

(证据卷二十七p43 孙某供述)

(证据卷二十七p46 孙某供述)
(三)从案发前后孙某的行为,也可以推定其不具备从事非吸犯罪的主观故意
根据会见时孙某陈述,2019年初,辖区派出所曾向其索要未兑付清单,在公司高层不配合警方的情况下,孙某自己于1月9日,通过微信提交了相关资料给警方。后来,经侦也曾索要相关资料,其时,孙某已离职,原下属给电话孙某征求意见时,孙某支持他们提供资料给警方[8]。
三、根据在案卷宗材料,同案29人中,23人的供述未提及孙某,另外6人的供述不能支持对孙某的实质指控,在案证据不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一)在29名同案人员中,易某某、袁某某、王某某、潘某某、王某1、陈某、宫某某、袁某某、王某2、陈某2、张某、汪某某、崔某某、杨某、赵某某、胡某某、杨某某、齐某等18名同案人在其讯问笔录中从未提及孙某
(二)部分提及孙某的同案人员,其供述不能证实孙某实际参与到了公司的日常管理,并起到了指挥、操纵、领导的作用
蒋某、王某某、司某某作为孙某的下属,其证言可以印证孙某在金某公司,主要负责线上APP的开发及运营,为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工作内容与信某集团的核心金融业务无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