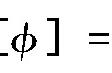(图片来自于头条图库)
回乡下,路两边,有一簇一簇火红的柿子,寂寞地挂在枝头,随风摇曳着。
猜想着,这些无人问津的柿子,努力地让自己丰盈甜美,可依然逃不过孤独终老的一生,就这样一直留在田野里,直至冬霜雪落,被鸟儿啄食,最终只能哀怨着归隐于大地。
记忆里我的童年时,久远的岁月里,柿子也曾是生活的宠儿,平淡日子的稀罕物。
记得是1982年吧,我上初中,被选上去地区教育局参加口头作文比赛,当时抽中的题目是——《我爱家乡的**》,准备时间是三分钟。
当时,我的脑海里涌现的,就是老家山沟里那一片片的柿子树,想起树上挂着的一个个如红灯笼般的柿子,许许多多的语句便出现在脑海里……
那天在赛台上,我侃侃而谈,从红柿子给我的视觉震撼,到它忍耐寂寞的坚韧品质,再到它带给人们的丰收喜悦,以及丰厚的经济收益,说不尽它的好,夸不完它的美。
待到结束时,依然意犹未尽,告诉大家来日再续——红柿之美。
那天,意料之中,凭借着这篇《我爱家乡的红柿子》,我挤进了决赛圈,并且获得了优异成绩。
事实上,家乡的那片红柿林,确确实实是我的心头宠,带给我许许多多的欢乐。
那时候,物质匮乏,孩子们的零食很少。中秋节前,柿子微红,姑姑们就会去沟里,在属于自家的柿树上摘一些生柿子,一半泡在院里的凉水罐里,一半放在热灶头的瓦盆里温着。三两天后,温水里的柿子就会变软,甜润可口;而凉水里泡着的柿子,则会在一个月左右去掉苦涩,变得酸甜脆爽,还夹杂着一丝麻辣味,特别好吃。那时候去学校,都是带凉馍馍做干粮的,要是能带个柿子配着,简直就是绝佳的美味。
过了中秋节,漫山遍野的柿子都红透了,凑个礼拜天,一家老小郑重其事地提着工具,去下柿子。大人们先拣能够探着的枝头小心翼翼地摘取,小孩子们则调皮地爬上柿树,专找那软乎乎的柿子来吃,揭开薄薄的柿皮,小嘴对着使劲吸溜,滑滑的果肉瞬间充盈在嘴里,满足得直嘚瑟。
一筐一筐的柿子搬回家,大人们便开始了深加工——旋柿饼。从邻居家借来几个旋柿饼车,捆扎在粗拙的木凳子上,把挑选好的柿子柄对着铁齿插进去,左手拿着旋皮刀紧贴着柿子顶端,右手飞快地摇着柿饼车的手柄,嘟噜嘟噜一阵操作,好看的柿皮像彩稠一样脱落,红红的柿子就变成了水润的柿饼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提着篮子里旋好的柿饼胚,去院子里撑好的席子上,一个个摆放整齐,等着太阳出来晾晒水分。
晒柿饼纯粹是靠老天爷赏脸的,太阳太毒晒出来柿饼太干,遇上连阴天柿饼会发霉呕烂,只有秋风吹着,太阳暖着,几天后柿饼胚才会渐渐变成深红,再一个个捏扁放筐里压着,隔几天再晾晒一下,反复几次后天气渐渐凉了,进入了冬季就要开始捂柿饼啦。
把晒好捏成饼的柿子整齐地摆放在院里的大缸里,最上面放上晒*柿饼皮,再用木盖压实,外面包上厚实的棉被,等上月儿四十,天空开始下雪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开缸查看柿饼出霜的情况了——好的柿饼外表霜白厚重,撕开来软糯拉丝,尝一口甜入心脾。
那时候,庄户人家都指望着自家的好柿饼,能够在供销社的收购点评个特等,卖个好价钱,就可以过个丰裕的年节啦。记得那时候,我妈在供销社,星期天我也会去收购站帮忙,听说我们那里的好柿饼都出口了,远渡重洋给国家换外汇啦。
谁知道,随着年代的久远,柿子的光辉历程竟然成了传说。我家的那三棵百年老柿树,已经有三四十年没有去照料了。村子里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老年人没有能力去下地收柿子,就那样由着它们自生自灭,孤独寂寞地一年又一年了。
如今,需要吃到上好的柿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冬日的集市上偶然遇见,我便会急不可待地买下来,放入冰箱慢慢回味。
想念家乡的老柿树,想念那一树树的红灯笼,想念曾经的那抹甘甜。
只是,柿子树再也不会有辉煌的时候了。

孤峰山的柿子树

去冬雪地里无人问津的红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