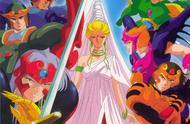图19:秘密经十四卷之摩利支佛母

图20:蒙文《甘珠尔》诸神之摩利支
在这些材料中,只有蒙文《甘珠尔》中的图像与乌拉盖的石刻基本一致,即七头野猪为正面向前跑的姿态,三面六(八臂)神的手中持物也与之基本吻和,其他的图像野猪或在一侧,或神为立姿,这是否暗示了蒙古地区流行的摩利支天的样式呢?显然,在别的地区供养的摩利支天与此种样式有区别。如那塘诸佛图像中的样式,虽然野猪拉车的形象略有相似,但女神是慈悲相的一面二臂坐姿相,西藏布达拉宫藏永乐款的摩利支天是一头大猪驮着三面八臂的女神,样式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因此,基本可以确定,在蒙古地区,供奉的摩利支天样式就是这种有七头小野猪拉车的坐姿三面六(八)臂像。但一个事实是,在内蒙流行的藏传佛教诸神中,摩利支天依然不是一尊流行的神。据一份材料记录,内蒙喇嘛教寺庙供奉的神,包括一、佛类,有过去七佛、五方佛、四方佛、六佛、三方佛、三世佛、佛的十大弟子、宗客巴;二、菩萨类,包括四大菩萨、六大菩萨、瞻部洲六庄严、二胜、密宗八十成就者、萨迦五祖;三、护法神、罗汉类,包括天龙八部、四大天王、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四、金刚神类,包括密宗五祖、五大金刚、八大金刚、金刚亥母、吉祥天母等[9]。显然,内蒙地区供养的佛菩萨诸尊,承续了藏传佛教的供养体系,摩利支天,不是常见的神灵。
摩利支天在历史上曾显灵:金人打开封时,北宋人逃难,皇帝之母带着一尊摩利支天逃到杭州,从此,此神,就有避兵难之说[10]。
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航海过程中,曾施印佛经,而他选印的佛经正是并不十分流行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台湾学者陈玉女在讨论郑和施印《佛说摩利支天经》的背景与动机时认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姚广孝题记郑和刊刻《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言:‘佛说摩利支天经,藏内凡三译。惟宋朝天息灾所译者七卷,其中咒法仪轨甚多,仁宗亲制圣教序以冠其首,然而流通不广。以广流通者,惟此本乃唐不空所译,其言简而验,亦多应菩萨之愿力。’”[11]
四
在藏传佛教流行的蒙藏地区,这样一尊并不常见的神像,是什么人将之立于这里的圣山之上的呢?首先排除的是个人信仰行为,对于这样一尊较大的、完全符合造像仪轨的石刻佛像,不大可能是个人信仰导致的结果。由于摩利支天具有镇山,保一方平安的作用,更多的是当地政府的行为。晚清时期,大约从 1901年至1913年间,共有四次土匪入侵,当时乌珠穆沁左翼王爷,为防土匪及外人入侵,保护一方平安,委托当地寺庙高僧,推断可能是农乃庙,因农乃庙为当时的旗庙,在双宝格达山的东侧的这座圣山上雕刻了摩利支像,并在每年特定的时间里由当地政府组织进行祭拜。
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从战事的角度来看,树立一尊麻哈嘎拉,即大黑天像才是合理的,而树立一尊并不常见的摩利支天像有些突兀。按藏传佛教传统,麻哈嘎拉,即大黑天是藏传佛教特别流行供奉的一尊神灵,同样在蒙古人心里这尊神灵也十分流行,他代表着战争的胜利。早在蒙元时期,麻哈嘎拉就是元朝皇室的护法神,是蒙古族的战神,是胜利的象征,元代每遇战事出征时,都要祭祀此神,以示旗开得胜。
元朝败亡后,这种信仰流传至蒙古草原[12],因此,如果为了防止土匪的入侵,树立象征战无不胜的麻哈嘎拉像似乎更加合理。鉴于此,笔者认为由当时政府树立此像有些牵强,就产生另一种推测,即此像可能是日本占领期间,由日本军人立于圣山之上,进行祭拜的。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地区,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在这个《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将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成立伪“满洲国”的意图。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并发表了《建国宣言》[13]。因此在日伪统治时期,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分别归伪“满洲国”和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强化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特别重视喇嘛教的工作,日本特务头目亲自到内蒙古地区活动,以笼络、结识一些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如日人菊竹,被称为“蒙古通”,精通蒙古文和蒙古语,自1921年开始就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情报工作,他经常穿着蒙古袍到蒙古各地旅行,结识了不少王公、活佛、大喇嘛,从而收集各种情报。
另外据日人幽径虎岩的回忆文章,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内蒙的一些具体工作。幽径为寺院出身,曾在佛教大学专攻佛学,入伍后任少校。昭和16年(1941年)任驻蒙军司令部副。赴任后,立即接受专门从事喇嘛工作的命令。工作之一是组织权威活佛访日,幽径虎岩在昭和17年(1942年)和18年(1943)先后两次有计划地组织权威活佛参观团访问日本,参观团的经费完全由军队机密费里开支。在日人的操纵下,昭和19年(1944年),以查干敖包寺活佛为首,以少数有势力的活佛为班底的喇嘛印务处正式起步。
日伪特务机关直接指挥或派遣“日本喇嘛”或日本特务冒充喇嘛到各大寺庙,以学习藏经、学习蒙古文蒙古语为名,长期驻在寺庙内,进行秘密活动。桥本光宝是日本研究蒙、藏喇嘛教的权威人物,1933年受日本方面的派遣到内蒙西部,以朝拜班禅喇嘛为由,长期住在乌兰察盟贝勒庙,并游历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等地喇嘛教各大寺庙,调查研究喇嘛教寺庙情况,联络喇嘛教界上层人物。
整顿喇嘛教,是日伪政权对内蒙古喇嘛教进行治理的既定方针,内容包括如下几项:一整顿思想,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和“日蒙亲善”教育;二设立伪满洲国“喇嘛教宗团”和伪蒙彊地区“蒙古佛教复兴会”、“喇嘛印务处”等组织;三削弱喇嘛教势力和影响;四参加生产建设;五设立喇嘛学校;六留日制度……据有关资料考查,日本在侵占内蒙古期间(1932年-1945年),以日本喇嘛或蒙古喇嘛身份,在内蒙古东、西部地区进行情报活动的有50余人,他们以“研究喇嘛教经典教义”、“学习蒙文蒙语”为名,在内蒙古各寺庙建立情报活动点,收集情报、控制喇嘛教界人士的行动。
摩利支天在日本,是专为武士所信奉的神。日本武将多数安奉摩利支天,这点引延至很多武家都供奉摩利支天,可以算是日本武者之守护神。摩利支天由唐朝传入日本后,被称为阳炎之女神,日本的武士相信摩利支天能够给他们带来武运,战无不胜。日本忍者由于经常进行密教修练,也将摩利支天作为自己的守护本尊.更重要的是因为摩利支天能够隐形,连天界的众多神明也看不到她的身影,所以修行隐身术的忍者都使用密教中的一个关于她的摩利支天咒和手印:摩利支天隐形印。
日本于20世纪三十年代占领内蒙北部,出于战争的考虑,树立摩利支天像进行供奉,以期得到他们认为的“武运”,可以“战无不胜”。但显然,乌拉盖的石像不可能是日本流行的样式。日本本土的摩利支天像可以推测出来。按唐代传入日本的密教像式,摩利支天可能主要是一种天女式样,即一手持扇,一手施与愿印的样式,不空译《摩利支天经》:“若欲供养摩利支天菩萨者,应用金或银或赤铜或白檀香木,或紫檀木等,刻作摩利支菩萨像,如天女形,可长半寸、或一寸二寸已下,于莲花上或立或坐,头冠璎珞种种庄严,极令端正,左手把天扇,其扇如维摩诘前天女扇,右手垂下扬掌向外,展五指,作与愿势,有二天女各执白拂侍立左右”[14]。
也就是说,这种摩利支天是手持天扇的天女样式,即没有猪车,也不是多面多臂式(参见前图8、9、10),按《大正藏》图像部七所存“唐本摩利支天”像为:三面八臂,立于一头猪身上,猪与摩利支之间还有一半月(参见前图11),但现存日本的摩利支天像可见为持天扇形,没有猪车,图式与不空译经中描述的样式一致(图21)。

图21:日本京都圣泽院藏高丽时期摩利支天图
但当时地处内蒙,接受委托的当地工匠可能依据了内蒙流行的样式雕刻了摩利支天像供于圣山上了。早在乾隆期间,在距圣山四五十公里的地方,建有三座喇嘛庙:侬乃庙、胡硕庙、佈林庙,这三座庙在日本侵略时,被日本人占作据点,或者是特务联络点,后被苏联红军炸毁。其中侬乃庙是旗庙,具有官方寺庙的意思。由此庙出具摩利支天的造像图样和委托造像工匠的可能性较大。
1945年,日人战败,同年,乌珠穆沁部道尔吉王与乌兰夫部冲突兵败,率6个苏木迁至蒙古国,圣山上的祭祀活动停止。日本现有三大摩利支天像。金泽的宝泉寺,上野的德大寺和京都建仁寺塔顶的禅居庵。分别属于真言宗、日莲宗、临济宗,各有其独自的渊源,造像的形象也各不相同。
五
中国崇奉摩利支天菩萨信仰的,多为王宫贵人,尤为皇室所尊重,此神极具有护国护王之政治色彩。自南朝《摩利支天经》传译中土以后,至南宋之前,未见广泛流传于社会大众,多行于皇室或官宦之中。南宋以后,由于中原战乱频仍,依赖摩利支天菩萨的信众渐趋转盛。就信仰状况而言,南宋因处偏安局面,故建康、永嘉等江南一带对于奉诵摩利支天经咒的需求,有顿时增多的景象……摩利支天菩萨以其护国、护王、护身,又极具战士特质,不仅为帝王所喜,也为将士所好[15]。摩利支天法,长期以来多为皇室、官宦或武将之家所奉持,虽不能说是为其所把持,但欲广传此密法于社会大众,可能非统治阶层所乐见[16]。
唐代或日本存天女执扇形摩利支天,可能出自不空译本,而藏传的多面多臂形,可能与天息灾译本和成就法所记摩利支天身形有关。画像和相关咒语的使用方法在当时是将像“戴于顶上或戴臂上或置衣中”。
乌拉盖地区发现的摩利支天,属于内蒙古地区所供养的摩利支天的独特样式,为坐姿,三面八臂式,七头拉车的小猪为向前奔跑的样子,它不同于西藏或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所供养的样式,当然与日本可能流行的唐代样式也完全不同。考虑到此神在内蒙藏传佛教中供奉的情况,推测可能不是信众树立的造像。树立造像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当地王爷为保一方平安而立像,二是日本军人为了所谓的胜利,从军人的角度,树立石像。而造像的工匠和图像样本可能来自内蒙当地,或者就是有旗庙地位的侬乃庙的僧人和寺内保存的图样。
另外,道教诸神中也吸收了摩利支天,在道教中此天被尊称为“斗母元君”,她共有九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和二儿子是“四御”中的“勾陈大帝”和“紫微大帝”,其余七个儿子就是“北斗七星君”。北斗七星分别掌管着所有人的生辰,人们只要虔诚底服从管辖他们的星神,就能得到该星神的保佑,保佑一生平安、顺利。
附录
《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 宋·天息灾译
今此真言亦能消除一切病苦,若人于其摩里支菩萨前作护摩者,而能增益象马财谷富乐之事,其作护摩者,若用酪酥蜜努里嚩草,作护摩一千遍,得人爱重无病安乐获财宝等,若以酪稻谷沙糖,作护摩一千能降夜叉女,若以芥子油[宁*心](切身)摩木,作护摩一千,能生冤家病。若以自身血,芥子油作护摩一千,能*彼冤家。若要却息除冤家灾,以乳汁作护摩一千,若要消除诸毒及降拏枳儞鬼,逐日诵摩里支心真言八百遍。
《佛说陀罗尼集经》 唐·阿地瞿多译 卷第十一《奉请摩利支天咒》
佛告诸比丘,若有人识彼摩利支天菩萨者,除一切障难、王难、贼难、猛兽毒虫之难、水火等难。若人欲行此法者,一切法中此法最胜。持此咒者,面向百踰阇那,一切鬼神恶人无能得其便者。若于难中行时,晨起诵前身咒,咒一掬水四方散洒及洒自身,若衣襟若衣袂若袈裟角一咒一结总作三结,即往难中行,连续诵咒(前二大咒)而行,所有一切事难军防主者,悉皆迷醉都无觉知之者。
《末利支提婆华鬘经》 唐·不空译
其造像法,一似天女形,身长大小一寸二寸三寸乃至一肘,其中最胜者一寸二寸为好,其作像又须得最好手博士。遣受八戒斋日日洗浴,着净白衣作之,其价直之者随博士语索不得违。作此像已,若苾刍欲行远道,于袈裟片中裹着彼像,若持五戒优婆塞,于头髻中盛着彼像,大小便时离身放着,不得共身上屏大小便利。
若比丘、比丘尼,袈裟中裹前像,若俗人头髻中着像,即作此头印以案像上,二十一遍诵呪行于道路,准前身印唯开二头指头二分许,即是护身印用之护身法。若人欲东西远行在路者,先作水坛,唤末利支安置已,取粳米华和酥,咒一遍一烧满一千八遍并诵咒,随所欲去处趣者得大验。又法若欲远行,先于私房七遍火烧熏陆之香并咒讫,着道行之时数数诵咒行者,路中贼难、鬼难等皆不得近也。又若畜生遇时气病者,于城正中央然谷树火,以牛乳火烧并咒即差,夜里应作此法,其明日午时还烧谷树火,取白芥子油与白芥子相和,火烧一千八遍并咒即差。
尔时末利支白佛言:世尊我有别法,今欲说者用好紫檀木广三指长三寸,其木一面刻作末利支形,作女天,其像左右各刻作两末利支侍者,亦作女形,复以别紫檀木作盖盖之,作此像已,欲行远道,将于此像不离自身,隐藏着之莫令听人知,日日数数诵呪。
《佛说摩利支天经》 唐·不空译
若欲供养摩利支菩萨者,应用金或银或赤铜,或白檀香木或紫檀木等,刻作摩利支菩萨像,如天女形,可长半寸,或一寸、二寸已下,于莲花上或立或坐,头冠璎珞种种庄严极令端正,左手把天扇,其扇如维摩诘前天女扇。右手垂下扬掌向外,展五指作与愿势。有二天女各执白拂侍立左右,作此像成,戴于顶上或戴臂上或置衣中,以菩萨威神之力不逢灾难,于怨家处决定得胜,鬼神恶人无得便。
《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 宋·天息灾译
卷一
彼菩萨手执针线,缝恶冤家口之与眼,令不为害。今有成就之法,用好彩帛及板木等,于其上画无忧树,于此树下画摩里支菩萨,身如黄金色作童女相,挂青天衣手执莲华,顶戴宝塔庄严。次别明成就法,令彼行人先作观想,想彼摩里支菩萨坐金色猪身之上身,着白衣顶戴宝塔,左手执无忧树花枝,复有群猪围绕,作此观已,若远出道路,如有贼等大难,以手执自身衣角,念心真言七遍加持衣角,复结彼衣角,冤贼等难不能侵害。
我今复说大摩里支降伏冤兵之法,若有国土被邻国冤兵来侵境土,时大国王若欲破坏调伏,于此成就之法深生信重,先请益阿阇梨如法供养,然叙所求之事。时阿阇梨为一切众生,发慈愍心入三摩地,彼曼拏罗中一切供献使用之物,并须周足,及同作法事之者不得阙少,于摩里支菩萨前,用白檀作曼拏罗,献白花烧香涂香并花鬘等,以酪乳砂糖作供养食,念献食等真言各七遍……四方作四门,及四维上下逐方写金刚器仗,令国王宰臣等,或颈上或臂上各戴一道,能与一切军众作大拥护,入阵之时刀剑等器不能伤害,获大胜捷。
又取河两岸上及十字道中土烧人灰,同和作冤兵主形,用前书者真言,安置在冤兵主心中,又取土或米面并黄姜合和作一猪,将前冤兵主安在猪口中,复用椀二只合其猪身,将诣冤兵之界,地下安置,以佉儞嚩木橛长八指,钉彼心上。以辛味酒肉等祭之。令阿阇梨乘象或乘车马,面向阵前列幢旗上,安摩里支菩萨像。身作黄色,阿阇梨头戴金冠身着黄衣,手执铃杵发大勇猛之心,复想猪车车乘,诵此禁冤兵真言八千,作忿怒相,冤兵自败,速得降伏。
复有成就法,能降他冤,拥护自众。于尸多林寂静之处,安摩里支菩萨像。于彼像前以衢摩夷作曼拏罗,献五种供养,随其自力,阿阇梨身着皂衣,顶戴皂冠,手执铃杵,发勇猛心,观想摩里支菩萨。作忿怒相,有三面。面有三目,一作猪面利牙外出,舌如闪电,为大恶相。身出光焰,周遍照耀等十二个月光。体着青衣,偏袒青天衣,光如大青宝等。身黄金色,种种庄严。臂有其八,右手持金刚杵、金刚钩,左手持弓无忧树枝、羂索。顶戴宝塔,立月转内。右足如舞踏势,左足踏冤家身。
卷二
复次大曼拏罗成就法行。
于曼拏罗中间安摩里支菩萨,深黄色亦如赤金色,身光如日,顶戴宝塔。体着青衣,偏袒青天衣,种种庄严。身有六臂,三面、三眼乘猪。左手执弓,无忧树枝及线。右手执金刚杵针、箭。
卷三
复有成就法降伏恶龙,若国土大旱必有恶龙,制伏云雨侵损苗、稼。
八臂、二足、三面各三眼,左右二面作猪相,黑色忿怒、颦眉、挂青天衣,耳环、指环、腕钏、脚钏、环珞铃铎等出微妙音,如是复有种种诸龙庄严,身上有黄龙王于其顶中,放摩尼光周回照曜。又此菩萨戴无忧花,发髻竖立,于其髻上复戴宝塔,又于塔中出无忧树,其花开敷,复于树下有白莲华。毗卢如来坐彼莲华,顶戴宝冠庄严发髻,面目端严,身真金色,结跏趺坐,执毗卢印,不动不摇如在定相,身有光焰,明照世间,安固不动,如无风之火,而复变起云中诸佛。左手执弓有无边德,牵其弓箭弦可至耳,第二手持嚩酥枳龙,口出二舌身如其线,第三手持德叉迦龙并无忧花,第四手作期克印并持羯里俱咤迦龙及索,右手持俱隶迦龙,第二手持钵纳摩龙并牵弓,第三手持大钵纳摩龙,亦出二舌并针线,第四手持商佉钵罗龙,以吉祥草缠龙手。
今此菩萨如童女相,面有三眼,身作黄色,乘黑猪,着青天衣一切庄严。左手作期克印,持无忧花并索,右手执针并钩。
S.2059《摩利支天菩萨咒灵验记》:
《摩利支天菩萨灵验记》讲述的是顶戴《摩利支天菩萨咒》后遇到的灵异之事。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十几件《摩利支天经》,有P.2805、P.3110、P.3136、P.3759、P.3912、S.699、S.2509、S.2681、S.5391、S.5392、S.5531、S5618、S5646、Дχ927、BD15098(来98,北8241)、BD15366、甘博16(3)、上博48(17)等等……敦煌文书中保存的某些《摩利支天经》是便于随身携带的册页装[17]。
《摩利支天菩萨咒灵验记》称撰写者山阴县人张俅早年曾周遊各地,在北方看到了《摩利支天经》,便于白绢上抄写摩利支天陀罗尼咒并长年虔诚顶戴,以致屡次得到神佑。文中讲述了两则故事。第一则谓咸通元年(860年)十一月张俅曾陷冰河,身体却不下沉,好象有人提着他将他送上了河岸,张俅由此得救并滞留河右为官。第二则称张仪潮收复凉州后,因军粮不足,张俅曾被差遣带领士卒往凉州送粮。待到达州治姑臧时,有省使五人正在凉州,他们本拟与完成任务后要返回原处的张俅一行同行,但省使们聚在一起商量后却认为张俅是一个书生,如果路上遇到贼人,张俅恐怕无力保护他们,不信任张俅的省使们遂决定迟一日单独上路。于是乎张俅率领着大队人马先行出发了。他们一路上逍遥自在,平安抵达了目的地。当随后而来的省使一行人到达前一日张俅等歇宿的沙沟时,张俅部下点燃的篝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孰料当天夜里这后到的一行人却遭到了偶然经过该地的吐蕃强贼的攻击,省使被捕*,各种损失难以尽数。……张俅称他总共在有强贼出没的河西道上走过二三十次,却没有输失,这一切都应归结为摩利支菩萨的加持护佑,所以他写下这篇序文,以劝谕后人[18]。
注释
[1] 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第30页,注2,提到(印度佛教)遗像流传至今的,据日人高楠篝村指出,出土于那烂陀寺址的摩利支天便是其中之一。
[2]见Dictionary of Buddhist iconography 卷8,第2253页Marīcī条。
[3]唐不空译《佛说摩利支天经》。
[4]宋天息灾译《佛说大摩利支菩萨经》卷二。
[5]参见Bhattacharyyab: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1987,New Delhi , 第95页-100页。
[6]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7]敖包,蒙语即石堆的意思,是祭祀之所。
[8]据文献载,嘎黑拉庙(嘎海里庙)在1942年日伪时期的统计中,还兴办了喇嘛学校,当时教员有2人,学生有20人。自德勒格编著《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2页
[9]自德勒格编著《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0-550页。
[10]据温玉成先生所说。
[11]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12]自德勒格编著《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元代对麻哈嘎拉的信仰源于巴思八,据该书所记:“初元世祖时,有帕斯八喇嘛用千金铸护法神麻哈噶喇像,奉祀五台山。后,请移于蒙古萨斯遐地方。又有沙尔巴·胡土克图喇嘛,复移于元裔察哈尔国祀之……元朝败亡后,此神像移至蒙古草原供奉。后来,由于察哈尔部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故归察哈尔部供奉。1634年,林丹汗兵败病逝之后,沙日巴呼图克图携带”嘛哈噶喇”佛像,到盛京献给皇太极……”。
[13]自德勒格编著《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以下日本在内蒙活动的相关材料也是出自该书。
[14]《大正藏》第二十一卷,二六一页b。类似的经文描述,参见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图像篇二》第475-476页。
[15]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16]同上,58页。
[17]扬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107页。
[18]以上内容,摘自前揭书,第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