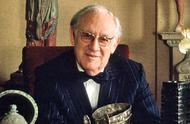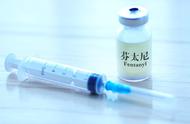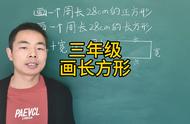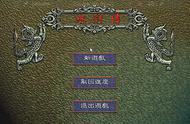拜耳广告
那个年代,结核病日益流行,医生手里没有啥特效药,所以拜耳公司为海洛因设计的广告语就是“不会上瘾的口服止咳药”。
但是,上瘾的病例日益增多,舆论沸腾下,政府立法对阿片类药物加以管制,逮捕给瘾君子开阿片类药物的医生,很快,没人再敢以身试法了,海洛因成了黑手党牟取暴利的“商品”,以及催生了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地的亡命毒枭。
海洛因的医用故事完结后,美国医生度过了对止痛类药物矫枉过正的几十年,即使遇到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也不会轻易服用阿片类药物,成瘾者被社会文化塑造成了异类。

疼痛或上瘾
1970年代,英国护士桑德斯,开办了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日常工作中,桑德斯接触了大量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病人,她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不能为了不上瘾而摧毁病人的人格,如果人之将死,让其有尊严地离去不是比防止上瘾更重要的事吗?”
在她的临终关怀医院里,晚期癌症患者可以获得阿片类药物的治疗,无论他们是否感到疼痛,桑德斯也因此被女王封爵。
桑德斯的探索影响了医学界对疼痛的看法,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一本书,用超过20种语言解释了疼痛治疗的步骤,还宣称摆脱疼痛是一项基本人权。
1972年,普渡制药下属的NAPP制药公司,开发出了一款定时缓释的吗啡药片,并被用于治疗临终病。
1984年,在NAPP的基础上,普渡制药发布了吗啡缓释片美施康定,该药主要用于癌症患者和术后患者。
医学的进步延长了癌症患者的生命,在这几个月至数年的生存期中,患者要承受治疗带来的疼痛,而美施康定就是响应桑德斯和世卫组织号召的“新药”。
1989年的一天,盐湖城圣十字医院进行了一场肺部手术,患者名叫多萝西。手术进行中,医生在多萝西的背部插入了硬膜外导管,并持续注射小剂量的阿片止痛药,之前此类药物一般用于孕妇分娩时。
手术结束后,多萝西的表现让医生们大为震惊,她完全不像典型的术后病人那样虚弱无力,而是自己站起来举手要了一杯咖啡,当时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在旁边观察她喝咖啡,“没有恶心,意识也很清醒。”
这个手术可以说是美国疼痛治疗的里程碑事件,阿片类药物不再被看作洪水猛兽,通过制药公司的创新,定时释放的药物可以持续缓解疼痛。
医生们在面对晚期或术后患者时,也不必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能提供的从安慰变成了真正的“希望”。

此后,医学界对阿片类药物的观点再次翻转:“既然阿片类药物能开给晚期癌症患者,那也可以治疗深受慢性疼痛所累的患者。”
八十年代末,医学杂志《疼痛》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被称为“阿片类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独立宣言”。
该论文指出:“通过对使用阿片类止痛药的38例癌症病人情况调研,只有两人出现成瘾问题,而且他们还都有吸毒经历。因此,并不是每个服用阿片止痛药的患者都会上瘾。”
这篇论文引发了部分医生的愤怒,他们学医时受到的教育是:
“绝对不能过量用药,要在最长疗程内给患者开最小剂量的药,不能让患者对药物上瘾。”
另一方面,论文作者也被一部分人看作为患者仗义执言的斗士、打破禁毒教条的先锋,他们用活生生的个案驳斥反对者:
“面对患有关节炎、滴酒不沾的奶奶、面对抽过大麻的纹身大哥、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养活一家人的建筑工人——这些被慢性悲痛折磨的普通人需要阿片类药物,你们怎么办?”
1990年,美国疼痛管理护理学会成立,该协会的口号是,“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这一口号马上获得了美国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的响应,把疼痛定为脉搏、血压、体温、呼吸之后,第五个衡量患者健康状况的指标。
美国医疗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也承认了这一认定,其中,加州药学会向其会员保证:“研究标明,正确使用阿片类药物的话,滥用的可能性极低。”

成瘾剂量
历经二十多年人们在疼痛和上瘾之间的“博弈”,普渡制药在1996年推出了镇痛类药物奥施康定 (OxyCon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