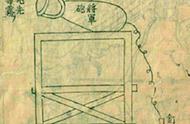悟空禅师肉身照。周奎提供
杨虎 / 文
路傍古时寺,寥落藏金容。破塔有寒草,坏楼无晓钟。
乱纸失经偈,断碑分篆踪。日暮月光吐,绕门千树松。
这首五绝,乃是晚唐哀帝时隐居在凤栖山白云深处的诗人唐求所作。诗中的古寺,即是指光严禅院。
唐求是个异人。他放着好好的青城县令不做,不买田,不造屋,每隔十天半月便骑着自家青牛慢悠悠往来于青城、临邛之间,访师求道,诵经听琴,往往至暮醺酣而归。方志上说,他非其类不与之交,写诗每有所得,不拘长短随手记下,成诗后即揉成纸团投入随身携带的大葫芦瓢中。因此也被后世称为“一瓢诗人”。
晚年卧病时,这位“一瓢诗人”把伴随一生的诗瓢投入味江之中,叹道:“此瓢倘不沦没,得之者方知我苦心耳。”随后飘然而逝。
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秋,正当锦官城内桂子飘香时节,朱椿忽然接到了来自南京的一封密函。纸上除“一瓢诗人”的这首诗外,再无只言片语,然而朱椿阅后却脸色大变,撇下正饮酒赏桂的一众后宫佳丽,匆匆离去。
初冬,永乐帝突然降下口谕:敕赐常乐寺名号为“光严禅院”,并赐半副銮驾、两口皇锅,以及龙凤旗、琉璃瓦、《初刻南藏》(即《洪武南藏》)佛经一部和印度梵文贝叶经《华严经》一部。又敕赐法仁名号为悟空。
车粼粼马萧萧。御赐诸物随即在严密的护送下,踏着江南初冬的第一场雪,往西蜀悄然进发。
为恭迎御赐经卷,经蜀王府倾力资助,光严禅院迅速在半山腰新起了一座飞檐翘角的藏经楼,楼内修藏经车一座,两旁殿宇叠错。昔日旧墙老瓦的寺院顿时黄瓦红墙,从山脚绵延到半山腰,后来便分为上、下禅院,繁密的木鱼声满山回响。
这一盛景,清嘉庆十八年(1813)的《崇庆州志》中是这样记述的:永乐十四年,蜀献王奏请,敕赐“光严禅院”,盖琉璃瓦。赐经文一大藏,计六百八十四箧。中竖藏经车轮,额曰:“飞轮宝藏”。
民国十四年(1925年)所修的《崇庆县志》更进一步描绘道:“(于是)经楼严肃,咨诸护法……红泉含影,青莲吐芳。”
世间唯一的这部《洪武南藏》就这样被不可思议的命运之手辗转遣到了山岚缈缈白云悠悠的西蜀光严禅院。从1371年除夕萌生于朱元璋的梦里,历经蒋山寺迁址、朱元璋离世、建文帝秘藏、永乐帝夺位……大明王朝半个世纪的烈焰已蒸腾烧灼得它伤痕累累。
然而它始终三缄其口。当它终于抖落一身风尘,从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煌煌禁宫逃逸进这一片静谧的山林时,一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它已经太累了,只想安安静静地憩息身心,听一听鸟鸣、雨滴、花落,然后在久违的佛号声中沉沉睡去……
它本来就是从清凉的世界里来的,历劫之后,终于回归了清凉--惟我佛慈悲--在清凉的那端,应得的那份大温暖正静静地等待着它。
所谓祸兮福兮。很多时候,悲欣间真的只隔了一层薄纸--人如此,书亦如是--1416年深冬的那个黄昏,当孤苦无依的《洪武南藏》随着马蹄得得,从落叶满地的山道上缓缓拐进光严禅院山门时,一双温暖的目光就定定地跟随了它。
那是悟空禅师的眼睛。
此后,那目光里的满腔慈怜将化为不朽的肉身,与它朝夕相伴--直至五百三十五年后,它离开,然后,肉身逝去。

四川省图书馆镇馆之宝《洪武南藏》。
2
就在《洪武南藏》与悟空禅师相遇时,山外,以它为底本刻印的《永乐南藏》正风行于世。而在它好不容易才逃离的紫禁城里,有一双眼睛正冷厉地监视着它。
这目光,据说和建文帝有关。
在1402年6月的大火中,当太监们指着地上那几具面目全非难以辨认的骨骸,说是建文帝等人的尸体时,朱棣的内心是暧昧不明的,明史里说:“(建文)遂阖宫自已焚燃。上(即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
为侄儿假惺惺地洒了几滴泪后,朱棣开始为自己辩解了:登位后,他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这样说:“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明实录·太宗实录》)。
然而史书的缝隙里却影影绰绰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让人们至今仍遐想不已:“上(建文帝)入宫,忽火发,皇后马氏暴崩。程济奉上变僧服遁去。燕王遂入宫。因指烬中后骨以为上。”
指认尸骨之后第八天,约1402年7月初,朱棣听取了学士王景的建议,将那几具无法辨认的尸骨宣告为建文帝、马皇后及太子,按皇室之礼予以了安葬。
对于失败了的英雄,人们给予着深深的同情。永乐帝登基之后不久,各地开始纷纷晃动起建文帝模糊的身影来。譬如明万历年间的《钱塘县志》这样记载:“东明寺在安溪大遮山前,建文君为僧至此,有遗像。”明代的钱塘县即今杭州市余杭区一带。今天,一副对联仍悬挂在该寺大雄宝殿前:
僧为帝,帝亦为僧,一再传,衣钵相授,留偈而化;
叔负侄,侄不负叔,三百载,江山依旧,到老皆空。
在众多的传说中,数光严禅院的情节有声有色:
当朱棣兵临皇宫,烈焰冲天之际,建文帝忽忆起先皇所授铁箱一口,遂开箱求法,箱内备有剃刀、袈裟,另有一信指出有一秘道直通宫外,并注明秘道入口,建文帝遂只身从秘道逃遁。
出宫之后,建文帝四顾茫然,慌乱中奔跑到一条河边,遂上船随水飘零。后辗转来到西蜀青城三十六峰深处的凤栖山常乐寺,投奔曾叔祖法仁避祸。
数年后,当东厂暗探追踪而至时,建文帝已迅速逃离。在他住过的禅房墙壁上,题了一首诗:“沦落西南数十秋,萧萧自发已盈头。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河无声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青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来休”。
又过数年,建文帝辗转滇、黔、巴等地后,再次回到了常乐寺。这时的常乐寺已更名为光严禅院。在悟空禅师劝导下,建文帝把自己关进了藏经楼里,苦苦寻求解脱之道。青灯下,黄卷中,昔日九五之尊已如梦如烟,建文帝感慨万千:
“阅罢《楞严》馨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阐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时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在《洪武南藏》浩繁经卷的启示下,建文帝终于潜心向佛,此后便从未离开光严禅院,圆寂后葬于后山。
或许,这传说的来源不仅因为朱椿是建文帝的姑父,也因了悟空禅师的渊源,更因了方孝孺的那番话:“燕王兵急。孝孺告帝曰今天下惟蜀王不背朝廷,其地四塞。今决一死战,不利,则收士、幸蜀,万一可图也。”
……天地悠悠。建文帝的传说至今仍缥缈在凤栖山一带,模模糊糊,真假难辨,就像那山间幻变不定的雾岚。
如果这位悲情皇帝真的在此渡过了最后的岁月,那其实是他灵魂最好的安息。不信你听,那白云缭绕的凤栖山间,千百年来一直随风飘荡着“一瓢诗人”潇洒的歌吟:“君不见,自古帝王多罪孽,怎胜清风润人间……”
3
静静地享受了二百年的太平后,《洪武南藏》再一次遭受了兵火之灾。此后三百年,山外彻底失去了它的消息。
这一次,大火发生在甲申年。
最初的消息,是北京城里崇祯皇帝吊死在了煤山。然后,整个中国都着了火--满清铁骑从山海关外黑压压冲进中原,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江阴惨*、常熟之屠、湘潭之屠、南昌之屠……直到今天,无数死者的眼睛仍在历史的夜空里不屈地圆睁着,喷发出惨烈的光芒:
扬州城中“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嘉定城里“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军将汉人妇女“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
昆山城被“*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啼哭)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
光严禅院遭受的则是张献忠大军的焚火。1644年八月初九日,张献忠大军攻克成都。朱椿的第九世孙、末代蜀王朱至澍投井自*。随后,张献忠大军西出成都,一把火烧了青城、温江等州,然后渡岷江,直扑崇庆州,知州王励精在烈火中触刃而死。
青城三十六峰寺庙、道观都被兵火焚毁。光严禅院虽境况稍好,也处处残垣断壁:“入后甲申大变,余殿无存,惟藏经车、藏经楼未遭灰烬外,琉璃瓦犹多存积,悟空法像犹如故也。”
张献忠的大军最终止步于莽莽苍苍的龙门山脉下。他望了望成都西北边那悲愤挺立的群山,回过头,在成都余余烟缭绕的废墟上沐猴而冠,称帝过瘾,然后大开*戒。
命运既已让《洪武南藏》入了山林,当蜀王自*的消息传来,名为海牛法师的住持立刻率领寺内众僧肩挑背扛《洪武南藏》奔赴汉藏边境的雅安天全县善居寺,万千惊恐之后,总算替哀哀无告的人间存住了那孤苦经卷、慈悲种子。
多年以后,在描述这次生死存亡的大迁移时,海牛法师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肩上经卷的沉重、脚步的惊惶,而是从凤栖山到大雪山善居寺的山道上,始终月色腥红,映照着四百余里山色林木由青翠入苍黄再至雪色苍茫。
六 、万物皆有因果
1
二十二岁之后,吕澂终于醉心佛学,开始了对佛教经籍版本的勘验、比对。
在此之前,这个江南青年的理想是做一名美术家。1915年,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教务长的他注意到了宗白华提倡的“生命美学”,极为振奋。三年后,他在《新青年》第六卷发表了名为《美术革命》的文章,引起陈独秀热烈反响,随即卷入了国内美术界“国粹派”与“革新派”的漩涡之中。
其时境外列强环伺,国内则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内心的挣扎苦痛终于将身心俱疲的吕澂引向了佛禅的空澄之境。1918年,著名佛学居士欧阳竟无渐准备南京在筹办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吕澄应邀协助工作,从此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得了一个绰号 “鹙子”,那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弟子舍利弗的汉译名字。
1937年春,抗战烽火逼近南京。吕澂随学院迁移到四川江津县。将士们在前线抗敌,吕澂在昏暗的油灯下废寝忘食地比对、查勘历朝以来的佛学经卷--“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天下者,中国文化也。只要文化不灭,中国就一定不会亡!
怀着这种悲愤激越的心情,学院专设了“访经科”。1938年初,日寇在南京大屠*中令人发指的罪行陆续传来,悲愤莫名的吕澂更加尽全力搜寻散落在各地寺院、民间的佛学典籍。这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名叫释潜遵的和尚专程从数百里外寄来的厚厚一本经卷抄目摹样,随信还附来了一句话:“国难当头,请为我中华佛学保存一缕血脉!”
1938年秋,一条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在西蜀深山中沉睡了五百二十二年的佛宝惊现尘世!
在后来名扬四海的那篇名为《南藏初刻考》的文章中,吕徴先生经过慎密的分析,考定数百年来一直藏身于西蜀凤栖山中的那部典籍就是遁世已久的《洪武南藏》。他写道:“明南藏始刻于洪武间,版成旋毁,后世未尝见其本也……天禧寺以永乐六年焚,崇殿修廊悉为瓦砾,经版当随以俱烬。厥后重修寺宇,改称报恩,藏经亦改编复刊,故明初数十年间大藏得有两刻也。初刻流传极暂,后世所见南藏皆永乐本,而又误认为洪武时刻,遂无知两版异同者。”
2
如果不是吕徴,光严禅院第四十四代住持灯宽老和尚或许一直也不会知道,自己每年都要在阳光下翻晒的那数不清的经书们竟是人们找寻了五百余年的、中华佛经里的国之孤本。
在漫长的年月中,《洪武南藏》渐渐失掉了自己的名字。不知什么时候起,寺里的僧人们开始把那浩繁的经卷简称为经、经书;如果遇到较为重要的场合,他们则又有些自得地宣称,自家藏经楼里有着明朝的龙藏。龙即是皇帝的意思,意思那经书的来头与大明的朱皇帝们有着关连。然而任是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尽管如此,一代又一代的僧人们每年夏天都会庄重地参与到寺庙的最重大的仪式--“翻经”中。那方法极为原始,趁阳光正好,把经书们从藏经楼里一担一担地担到大殿前的空地上,铺上一层慈竹编制的晒簟,然而用烟熏过的特制竹片一页一页地翻(不能用手,因为怕手出汗)。有重页和漏页者一旦发现,得去悟空禅师肉身灵塔前低头,合十忏悔。待经书一页页晒透后,再仔细将防蛀的叶子烟夹到每一卷经书中。
每翻一次经,就要耗去几乎整个的夏季时光。并且,光是叶子烟就需要去山下采买几百斤。
从7岁起就在光严禅院出家的灯宽记得,翻经季节,每每忙完一天的晾晒时,已是落日时分。金黄的夕照中,晚课的暮钟悠悠敲响了,抬起头覷眼一望,梵天里都是荡漾的钟声……
转眼到了公元1951年。这一年,正在北京忙于“中国佛教协会”筹建工作的吕徴特别繁忙,然而他一直念想着那远在四川的《洪武南藏》。新旧更迭,全新的社会对珍贵的佛教典籍有了与千百年皆由寺院保存不太一样的做法。他听说像新成立的扬州图书馆已经将一部完整的《永乐南藏》请进了设备良好的古籍珍本室,心里隐隐有了兴奋的预感--渡尽劫波之后,《洪武南藏》终将功德圆满。
7月,从成都传来消息,1951年6月的一天,四川省崇庆县首任县长姚体信根据县志记载,亲临光严禅院,直奔藏经楼,在楼中认真翻阅、察看了《洪武南藏》后,出来表示:因为土改政策,住持灯宽已被划为大地主,光严禅院众僧人面临遣散,寺中已无人力财力能保存如此卷秩浩繁的国宝。
姚县长当即命令封闭藏经楼,将经书装箱,随之派人请省里的文物专家进行鉴定。随后,县里征召了上百名挑夫,把重达三吨的佛典一路担到成都,放入了四川省图书馆永久存放。
2003年暮春,在与来访者谈到此事时,历经坎坷,重又回到修葺一新的光严禅院担任主持已近二十年的灯宽感慨道:“这姚县长是护法金刚转世吧?一般当官的可没这种觉悟。”
然后他顿了顿,叹道:“万物皆有因果。”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ihxdsb,*3386405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