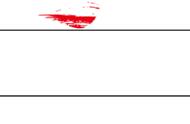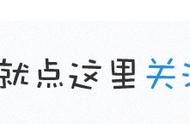当年的第一保育院分大班中班小班,当年我3岁,上小班,有一次觉得我睡的那个小床有点小,那个床我头顶在前边脚踩在后边,头顶上后脚能踩到后边。我把这事给父亲说了。父亲礼拜一送我去时把这事给阿姨提了意见。俩阿姨表情怪异,然后嘀咕了一下,把我俩领到中班去了,然后指着一张床让我躺上去试。我一试当然是很宽松的,阿姨就说是现在这小孩子都能撒谎,你怎么就随便说我们呢?我试那张床根本不是我的,等于是阿姨把父亲蒙了。父亲也是粗心大意,因为小衣服小被褥上应该绣有名字的。

当年每次接送我的都是父亲,后来问到此事,母亲说她骑自行车不老练,会上不会下。有次在钟楼下邮局附近刹不住差点撞到交警,大喊道同志快把我的车子拉住。当年有种自行车是倒蹬闸。

保育院的大门坐西朝东是木栅栏式的,我觉得跟动物园的大门差不多,大约有1.8米宽,两米高,经常挂着铁锁,门外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麦地里有条曲曲弯弯的土路,门边有一株高大的槐树。父亲蹲下来拉起我胸前别针别着的手帕给我擦擦鼻涕,在我手里塞了一块水果糖,用带烟味有胡茬的腮亲亲我,然后就推着那辆唏哩哗啦乱响的旧自行车走了。

我看着父亲瘦弱的背影,他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蓝色旧中山服,偏身上了自行车逐渐远去,慢慢消失在尘土弥漫的麦地细细弯弯的小路上。面对陌生的阿姨和一个也不认识的小伙伴们,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恋父情结。这时有几个孩子哭了,我于是哽咽着也哭了。我是哭哭涕涕的被阿姨哄着抱进了屋子。进院子的时候,我看见了门房的那部老式的黑色拨号电话机,一头裹着红布,一头缠着胶布,这是保育院里唯一的电话。后来有一次,我见阿姨打电话,心里好奇,冷不防伸手模仿阿姨也拍了一下叉簧,贸然挂断了电话,惹得阿姨生了气,旁边的炊事员爷爷哈哈大笑着鼓励我道:厉害厉害。弄得好。把他家的!真是把他妈叫嫂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