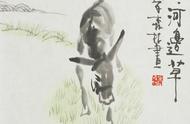彩绘连环画《白蛇传》,任率英绘
在小说另一处,许宣去承天寺游玩,遇见个道士,那人说他头上一团黑气,肯定有妖怪缠她,于是给了他一道符去烧。许宣那时也有点怀疑妻子是妖怪,就照做了,结果白娘子并没有现形,倒是丈夫的不信任令她颇为不满。为了出这口气,白娘子第二天便亲自去会了会那个道士,把他教训了一番:
那白娘子道:“众人在此,你且书符来我吃看!”那先生书一道符,递与白娘子。白娘子接过符来,便吞下去。众人都看,没些动静。众人道:“这等一个妇人,如何说是妖怪?!”众人把那先生齐骂。那先生骂得目睁眼呆,半晌无言,惶恐满面。白娘子道:“众位官人在此,他捉我不得。我自小学得个戏术,且把先生试来与众人看。”只见白娘子口内喃喃的,不知念些什么,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缩做一堆,悬空而起。众人看了,齐吃一惊。许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众位面上,把这先生吊他一年!”
白娘子的气愤不仅是因为害怕自己现出原形,更是因为这个道士侵害了她追求美满婚姻的权利。她念咒让道士悬空,也无意伤人,只是为了略施小惩,这番行为倒也确实显得活泼可爱,更体现出她的自尊好强。总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蛇虽然身上妖气尚未褪尽,但举手投足与人无异,民众对这一形象的态度已经转变为同情、肯定,而这为进一步的改写创造了空间。

清嘉庆刻本方成培撰《雷峰塔传奇》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给这个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基本定型,但“白蛇传”的大范围流行还是在清代:不仅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比如《西湖缘》、《后本白氏全传续姻缘》、《雷峰怪迹》、《雷峰塔奇传》等;而且频频登上戏曲舞台,最常演出的剧本主要有三种,都名《雷峰塔》,分别是黄图珌的看山阁刻本、梨园钞本和方成培的水竹居本——这当中属方成培所著的《雷峰塔》(又名《雷峰塔传奇》)最具代表性。方成培著《雷峰塔》在当时众多剧本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桥段,包括端午、盗草、水斗、断桥、生子,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充实,戏剧冲突也得到强化。在这个本子里,白娘子的形象进一步演变,妖气已经褪尽,成为一个美善兼备的女人。白蛇本在西池蟠桃园中修炼千年,即将修成正果,只因前世和许宣有宿缘未解,慕恋红尘,决定前往人间寻觅有缘之士:
今日慧眼照得震旦峨嵋山,有一白蛇,向在西池王母蟠桃园中,潜身修炼,被他窃食蟠桃,遂悟苦修,迄今千载。不意这妖孽,不肯皈依清净,翻自堕落轮回,与临安许宣,缔成婚媾。那许宣原系我座前一捧钵侍者,因与此妖旧有宿缘,致令增此一番孽案。但恐他逗入迷途,忘却本来面目。(第二出 付钵)
虽然苦苦追寻许宣只是因为前世有缘,但是白娘子对丈夫却是饱含至情,对白之间情深款款:
〔生〕既蒙娘子雅爱,使小生不胜感激。〔旦〕官人说那里话。
只因你意酽情浓,只因你意酽情浓,致挑奴琴心肯从。自今呵,喜丝萝得附乔松,愿丝萝永附乔松。(第七出 订盟)
当白娘子误饮雄黄酒现出原形,不巧看见的许宣直接吓死在地,叫也叫不醒。心急如焚的白娘子只好奔赴嵩山,冒着生命危险盗取九死还魂仙草;当许宣听信法海的说辞,白娘子怒骂他拆散夫妻、毁人姻缘,便叫水族大作水势,淹没金山。这些新添的情节,都尤显出白娘子为爱付出之深,对比之下许宣则显得十分薄情,整个剧对他也是处处暗贬,由此更衬托出白蛇的正面形象:
<商调集曲·金落索>〔金梧桐〕<旦>我与你噰噰弋雁鸣,永望鸳交颈。不记当时,曾结三生证,如今负此情,<东瓯令>背前盟。〔生白〕卑人怎敢?〔旦唱〕贝锦如簧说向卿,因何耳软轻相信?〔拭泪起唱介〕<针线箱>摧挫娇花任雨零,<解三酲>真薄幸。<懒画眉>你清夜扪心也自惊。〔生白〕是卑人不是了。<寄生子>〔旦〕害得我飘泊零丁,几丧残生,怎不教人恨、恨!(第二十六出 断桥)
方成培《雷峰塔》剧本的另一个重要改变,就是为故事增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白娘子被压在塔下二十余年,她的儿子许士麟也已长大成人,甚至高中状元。可是皇帝不允许拆毁雷峰塔,许士麟只能到塔前作一番祭奠,他因母亲蒙冤而痛哭,孝感动天,连佛祖也深受感动,决定宽赦白蛇的性命,让他们一家人重聚首:
世尊若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能忏罪则见睍俱消。士有百行,以孝为先,感格诚如舍矢中的。咨尔白氏,虽现蛇身,久修仙道。坚持雅操,既勿惑于狂且;教子忠贞,复不忘乎大义。宿有镇压之灾,数不过于两纪。念伊子许士麟广修善果,超拔萱枝,孝道可嘉,是用赦尔前愆,生于忉利。自此洗心回向,普种善因,可成正果。(第三十四出 佛圆)

梅兰芳主演剧目《断桥》剧照
方成培的《雷峰塔》吸取了若干“白蛇传”剧本的优点,它被打磨得更为连贯、完整,拥有更高的口碑,对后世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包括梅兰芳主演剧目《断桥》、田汉剧本《白蛇传》、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在内的知名作品,都采纳了《雷峰塔》的故事框架。可以说,方成培的《雷峰塔》,是后世大多数“白蛇传”改编作品的底本。
三、白蛇故事的主题与形象
在先民看来,蛇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生物:没有四肢,蜕皮复生,来去无踪。所以早期的人类对蛇是既恐惧又敬畏:一方面,人们认为蛇很凶残,不易靠近,把它想象为邪恶的象征;另一方面,蛇又具有神秘的色彩,在上古神话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至今能看到许多“人蛇合一”的传说(比如女娲),同时在传统社会里,蛇很多时候也是吉祥的征兆,看见蛇或许预示着财富、寿命的增益。关于蛇,值得留意的一点是:蛇身形柔软,喜居阴湿,而古人由此联想到了女人的特征,把蛇和女性联系在了一起——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蛇精往往都是女人,倒不是说记载中没有男性的蛇怪,但是“女蛇精”的形象一旦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就逐渐固定成了民间怪谈里的一种套路。在今天看来,上述蛇的那种两面性,和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对情欲的矛盾心态颇有些相似:一方面,天理不可违逆,但人欲也不可消除,所以人们有时也承认异性的魅力;另一方面,在传统道德的教训之下,人们又接受了禁欲主义的观念,害怕自身被情欲所毁。无疑,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书写中,对自身情欲的矛盾心理,往往表达为男人对女人的幻想与恐惧。

1992年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剧照
纵观白蛇故事的发展,能清楚看到故事主题经历了从“禁欲”到“崇情”的转变。早期的白蛇故事,即本文举出的《李黄》、《西湖三塔记》,无一不在劝人克制自身的*,小说中的白蛇直接被塑造成淫邪的象征,所谓淫荡且邪恶,必然会招致严重的后果,这毫不隐讳地表达了对女性的否定和贬低。甚至连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也不例外。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冯本的落脚点仍在禁欲:佛教思想的代表法海最终成功制服白娘子,千年万载不许出世,而许宣也自愿出家修行。小说末尾,法海留下了八句诗,颇能为全篇定调:“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然而这或许不能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小说实则给白蛇故事的解读带来了新的可能,有什么东西正要冲破禁欲主义的藩篱。实际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跟“禁欲”几乎沾不上边,它成功塑造了一个美丽而直率的白蛇形象,白娘子的*和人格第一次受到了肯定,就像作者冯梦龙自己也推崇人间“至情”,称“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显然,这一切都折射了明代肯定人欲、寻求人性解放的思潮。由此发展到清代,众多白蛇故事(比如方成培的《雷峰塔》)便开始毫无保留地赞美白娘子追求爱情的权利,毫无保留地谴责法海拆毁他人姻缘的行径。到这里,“白蛇传”作为一个爱情传说的本色,也最终固定了下来。
与故事主题的演变相称,白蛇的形象也经历了从“妖”到“人”的转变。早期的白蛇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妖怪;当然,并不是所有民间故事里的妖怪都作恶多端,不过人们的确把白蛇塑造成了一个淫邪的毒妇,专门残害年轻男子。可见,这个时候的白蛇形象非常扁平单调。而如前所述,情况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就有所变化:白蛇身上兼具人性和妖性,言行举止更接近一个现实的女子,不过仍保留了一些妖精的凶恶气,比如小说写许宣相信法海说她是妖精所变,白娘子勃然大怒:“若听我言语,喜喜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这种恐吓姿态倒是与《西湖三塔记》里的蛇妖很接近了,不过白娘子也没有真的大开*戒,于是这些话反倒从侧面体现了她的独立人格和叛逆精神。这或许说明,在明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尚需要以“妖怪”的身份作为中介,才能得到较为顺畅的表达,毕竟在大众的想象中,妖属异类,可以超离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并因此寄托着人们被压抑的观念。到了清代方成培的《雷峰塔》里,白娘子虽然还是个“妖孽”,但那股妖怪的凶狠劲已经荡然无存,而是蜕变为一个绰约多姿、秀外慧中的理想女性,一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牺牲者和受难者,正所谓“觅配偶的白云姑多情吃苦”。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过去,《雷峰塔》里的白娘子多了一重新的身份:母亲——事实上,按照剧中如来的说法,“念伊子许士麟广修善果,超拔萱枝,孝道可嘉,是用赦尔前愆”,白蛇犯下了与人类通婚的罪行,她没有能力自行推到雷峰塔,是她的儿子才为她争取到了上天的宽恕。正是作为一个母亲,而不是作为一个女人,白娘子才得到了救赎。所以,与其说《雷峰塔》中的白蛇是一个理想的女子形象,不如说她是一个契合于传统纲常伦理的贤妻良母,而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局限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