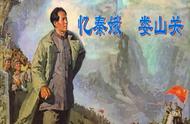三:篆刻市场的主体是职业印人,其次是从事书画或其他职业的兼职印人,官员和家境殷实者一般不“鬻印”。
清季,鬻印或间接鬻印的印人不胜枚举,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观念的制约,所见篆刻史料中,对此多是一笔带过,或者避而不谈,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
通观清代篆刻市场,丁敬只是创造了润格纪录,邓石如则完全依靠卖印游食一生,允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邓石如(1743~1805年),安徽怀宁人。性廉介,“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以书刻自给,遍游山水。邓出身寒门,九岁辍学“采樵返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何绍基书《完白山人墓志铭》)。杨沂孙《完白山人印谱》序称“效其父为篆隶,摹其印卖诸市”,17岁就开始写字刻印谋生。他曾鬻刻至寿县,在梁巘书院前摆摊写字刻章。梁看见他的书法大赞:“其笔势浑鸷,余所不及,究其才力,可輘轹数百年钜公矣。”(穆孝天、许佳琼著《邓石如》)邓因此得识梁巘。后梁氏又将他推荐给金陵梅氏兄弟。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记道:“山人既至,举人以巴东故,为山人尽出所藏,复为具衣食楮墨之费。”他在梅家断断续续住了八年,“学既成,梅氏益匮,不复能客山人,山人乃复如前,草履担簦,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在大约三十余年时间里,邓石如鬻书卖印足迹遍及苏皖江浙,结识了如曹文埴、毕沅、刘墉、王文治、钱坫等高官大儒,与他们订交来往,受益无穷,也收益颇丰(黄秀英、秦金根《从邓石如的游学与交谊看其书风的形成和影响》)。晚年,他回到故里,用鬻印的积累买良田40亩并建屋一栋,颐养天年。其子邓传密《东园还印图序稿》中称父亲:“刻印则惟壮年前后事,时情殷负米,徒以上世法书,不能博流俗所好,藉刻印取值。”显见,当时邓石如书名不显,是靠刻印谋生并藉此游历天下。

另一位具有“戏剧性”的人物是巴慰祖。巴慰祖(1744~1793年),字予藉,号莲舫,歙县渔梁人。巴氏家族为大盐商,在扬州有巨大的产业。《扬州画舫录》卷十记载,巴氏家族“来扬以盐荚起家,好游湖上,家有画舫”。画舫相当于现在的私人豪华游艇,巴家有“莲舟”、“莲舫”等数条画舫。少年时巴慰祖的父亲一直反对他刻印,认为百无一用。巴虽曾捐得候补中书虚官,由于他不善经生,终致晚年家道衰落。不想他却靠鬻印卖字收入颇丰,仍然衣食无虞。其晚年经历成为“鬻印”为生的成功典范和当时篆刻市场繁荣兴旺的最鲜活的例证(《徽州艺事》五)。
四:初步总结清代篆刻市场,有几个明显特点值得注意:
1.“鬻印”为生的印人众多,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职业阶层。
篆刻市场的繁荣,保障了印人的生存所需,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壮大了印人队伍,从而刺激、促进了篆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2.印人身份构成丰厚,层次提高。
身份的转变使得印人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晋身于文人、艺术家行列,从而导致了印人和篆刻艺术地位的提升,也促成篆刻逐步向独立的艺术门类发展。
3.篆刻价格高于书画。
清初至晚清前后,古印的价格高于古书画,印人的润格也高于古书画和同期书画家。
4.印人润格出现,标志着印章已经成为独立的艺术商品进入市场化操作,价格体制、市场机制初步形成,篆刻市场发育相对成熟。
5.印人生活状态优良。
为印人生存和创作以及保持艺术独立性提供了保障。钱泳记述:“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年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钱泳《履园丛话》)万寿祺刻三个石印能买约一石米(150斤),刻一个玉印能买良田一亩。另外,从丁敬润格、沈世上司以“四金”命刻、吴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姜恭寿“有以百金求篆而不得者”,以及邓石如、巴慰祖的经历和胡志仁籍印为八口衣食等记载看,清代名印人的收入相当可观,一般印人想必也有不低收入。否则,科举不利者也不会纷纷转而去工“图章”了!
文 | 陈岩
来源 | 中国书画
声明 | 图文来源网络,旨在分享传播,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原文仅代表原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书艺公社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三十日内与书艺公社联系。
END
好物推荐
——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