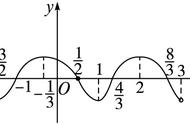《竹里馆》为五言古绝,总共也才四句二十个字。王维这短短四句平常字词,选取了一些在辋川,甚至是人间常见的意象“幽篁”、“弹琴”、“长啸”、“明月”、“深林”,巧妙地构建出诗词艺术创作中的另外一个境界——无我之境。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无我”是相对于“有我”而言。什么是“有我”、“无我”?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做过阐叙: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这话不难理解。“有我”,即是“以我观物”,而“无我”,则是“以物观物”。
有我之境,就是诗人写诗人自己的活动和情感;无我之境,就是诗人把自己当成客观对象来描写。

诗言志,诗就是诗人感情的抒发。那么在作品中带入作者的感情,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作者要表达的内容,这是诗词创作的本心,也是创作者最容易达到的境界。是故一首诗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而不论好坏基本上都自带了诗人的态度、情感。就好比一位小说家,一般第一篇小说都是自传,因为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身边的人物、代入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初级作者都具备的能力。
这就是“有我”的创作方式,到了一定境界之后,作者开始抽离自己的作品,写的内容不再与自己有关,就好像写侦探小说的,必然是写别人的故事,但是也需要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这种写作方式,就是“无我”——这里面没有我,但是暗藏了我的态度和情感。
“无我”比“有我”更难成就,但是并不代表“有我”、“无我”两种方式有高低之分。像李白终其一生,诗诗有我,可是气贯长虹,震铄古今,王维晚期作品篇篇无我,进入空灵境界,带给我们另外一个领域的情感极端感受——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共鸣的情境不同。

但是在表达上,“无我”确实要比“有我”更加难,因为这不是人类自带的技巧,而是修出来的。这也是同为田园诗人,王维和孟浩然的区别所在。孟浩然就是个大地主,对田园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爱,而王维的田园是逃避官场与人心的修行。这些情感的细微区别其实在作品中都可以发现。
这首《竹里馆》就是王维“无我”创作的代表之作,他选取的字词虽然常见,但都是指向冷、空、寂的意象。起句“独坐幽篁里”,这里是谁在独坐,谁在弹琴?好像是诗人,也更像不是诗人。即便是诗人自己,也如同一个画面中人物,“我”只是一个读者,远远地在看着。第二句“弹琴复长啸”,这是谁在弹琴,谁在长啸?还是不得而知,而且也不重要。
即使那个人是我,那也是一个躯壳的“我”,并非真我,他只是《竹里馆》这幅画里的一个人物,我们在画外看这这个人物的行为,融入整体画面的空灵、冷寂的意境,他的行为绝对是非常契合地溶解在这首诗里面的。
“我”在这首诗、这幅画里面只是一个让诗意更加委婉的道具,真我其实和读者一样,站在画外面,与诗无关。这种手法就叫“以物观物”,这种效果就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而后两句“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就更加是完全的景色描写,与道具的“我”关系都不甚紧密。所以说这四句其实都是写景,前两句有关联,是一个人物在绿竹林围绕的小馆里弹琴长啸,后两句是林深无人回应,只有明月相照。第一句和第三句都是静态描写,第二句和第四句都是动态描写。这两联诗用力是均衡的,但是又相互照应,如“相照”对应“独坐”,“明月”对应“幽篁”,“长啸”对应“深林”,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整体的意境还是控制在清幽的层面。
这首诗本身不是靠字词取胜,每一句用力都不猛,却妙谛天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
短短四句,每一句都有它不可或缺的地方。
如果说了这么多,还要坚持问哪一句最有意境,我只能告诉你,单独的哪一句都平平无奇。

这就是王维的水平所在,相比之下,和他一起在辋川隐居十几年的裴迪,也写了一首《竹里馆》,就是典型的有我之作,也可以很轻易地找出重点句子:
来过竹里馆,日与道相亲。
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
我到了竹里馆,每天都修道参禅。这里很安静,只有山鸟进出,幽静深远没有俗世众人。
这就是典型的“有我”之思——以我观物。
裴迪用自己的眼光带我们走进了竹里馆,并在最后一句“幽深无世人”为整首诗,整个竹里馆下了一个“幽静”的定义,那么这一句自然是这首诗的重点。
不过这和王维的《竹里馆》,就是云泥之别了。说句不客气的,我们今天大批写旧体诗的人也能达到这种水平。
可我们和王维的差距,那就是天差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