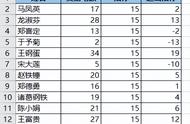老虎的金黄
那威猛剽悍的孟加拉虎
从未想过眼前的铁栅
竟会是囚禁自己的牢房,
待到日暮黄昏的时候,
我还想无数次看到它在那里
循着不可更改的路径往来奔忙。
此后还会有别的老虎,
那就是布莱克的火虎;
此后还会有别的金黄,
那就是宙斯幻化的可爱金属,
那就是九夜戒指:
每过九夜就衍生九个、每个再九个,
永远都不会有终结之数。
随着岁月的流转,
其他的绚丽色彩渐渐将我遗忘,
现如今只剩下了
模糊的光亮、错杂的暗影
以及那初始的金黄。
啊,夕阳的彩霞,啊,老虎的毛皮,
啊,神话和史诗的光泽,
啊,还有你的头发那更为迷人的金色,
我这双手多么渴望着去抚摩。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Ⅰ:博尔赫斯(节选)
文 / 罗纳德·克莱斯特
博尔赫斯相当内敛。他离群索居,甚至隐忍自贬。他尽其所能地避免提及自我;当被问到有关他自己的问题,他都迂回作答,去谈论别的作家,引用他人的话甚至他人的著作来间接表述或掩饰自己的思想。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刚开始着手写小说时,你很胆怯,无自信?
博尔赫斯:是的,我很忐忑,因为年轻时我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所以我就想:“如果我写小说,所有人都会看出我是个外行,我是在闯进一片禁地。”后来我在一次意外中受伤......如果不是因为脑袋受伤昏迷过,或许我永远也不会去写短篇小说。
《巴黎评论》:而且,或许你的作品也永远不会被翻译成其他文字。
博尔赫斯:那样的话,也不会有人想到要翻译我的东西,所以这次事故我是因祸得福。这些小说,不知怎么的,反正时来运转,有了市场,被译为法语;我获得了欧洲的伏蒙托文学奖,后来作品好像就被翻译成了许多种文字。我的第一个译者是伊瓦拉。他是我的一位好友,是他把我的小说译为法语。我想他大概将那些小说加工改良了很多,不是吗?

《巴黎评论》:伊巴拉是第一个译者?不是卡卢瓦吗?
博尔赫斯:他和罗杰·卡卢瓦都是。在迟暮之年,我开始发现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对我的作品有了兴趣。这看起来有点怪异:我的很多文字被译成了英语、瑞典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葡萄牙语,还被翻译成几种斯拉夫语,以及丹麦语。而这对我来说始终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我出版过一本书——那肯定是很久以前了,我想是在一九三二年——结果到了那年年底,我发现终于有至少三十七本卖出去了!
《巴黎评论》:那本书是《恶棍列传》?
博尔赫斯:不是,不是。是《永恒的历史》[又译作《论永恒》]。起初我想找到买这本书的每一个读者,为此书向他们说抱歉,另外也为他们垂顾此书而表示感谢。这里需要来一点解释。你可以试着设想一下这三十七个人——真实的大活人;我意思是说他们每人都有着一张只属于他自己特有的面孔,他自己的家庭;他住在某条特定的小街上——因为他的存在,那小街便似乎只属于他的。但是,如果说你的书卖出了,假定两千本吧,这就跟你的书连一本都没卖出去是一码事,因为两千这个数字太庞大了——我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对两千个读者都有着具体的想象或印象。而三十七个人——也许这也太多,或许十七个甚至七个会更好——但三十七个就仍然在一个人的想象范围之内。
《巴黎评论》:说到数字,我注意到在你的小说中有些特定数字重复出现。
博尔赫斯:哦,是的。我极度迷信。我觉得这有点羞耻。我对自己说,迷信毕竟是,一种轻微形态的疯癫;我想是这样的,不是吗?...
《巴黎评论》:你会不会说,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也就是迷信,才让你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用同样的颜色,红、黄,还有绿色?
博尔赫斯:不过,我用绿色了吗?
《巴黎评论》:用了,但用得没有其他颜色多。你看,我做了一点相当琐碎的工作,数了那些颜色,在……
博尔赫斯:不,不用了。那是“语言文体论”,西班牙语的说法叫“estilistica”,这种学科这里也有人研究。我想你会发现黄色。
《巴黎评论》:还有红色;经常变化移动,渐渐褪色成玫瑰红。
博尔赫斯:真的吗?我倒是从没注意过。
《巴黎评论》:今天的世界仿佛是昨日之火的灰烬——这是你用过的一个隐喻。举个例子,你说过“红色的亚当”。
博尔赫斯:“亚当”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我想是“红土”吧。另外,“红色的亚当”这个词听起来很入耳,不是吗?用西班牙语说就是RojoAdan。
《巴黎评论》:听起来确实不错。但那不是你试图表达的意思:颜色的运用是一种隐喻,寓意世界的退化堕落。对吗?
博尔赫斯:我没有试图表达什么。我没有意图。
《巴黎评论》:只是描述而已?
博尔赫斯:我就是描述。我只管写作。说到这个黄颜色,有个视觉生理的解释。我的视力开始恶化几乎失明时,我最后看到的颜色,或者说最后突出呈现在我眼中的颜色——当然了,我现在还能分辨出你的外套颜色与这张桌子或你身后木头家具的颜色不同——是黄色。黄色比其他颜色突出,因为它是最鲜明生动的色彩,所以你们美国的出租车就是黄色的。出租车公司最初其实是考虑用猩红色的,然后有人发现在晚上或者有雾的时候,黄色比猩红色更显眼,所以你们就有了黄色出租车,因为所有人都能一眼辨认出这个颜色。当我视力衰弱,逐渐失明,当世界在我眼前褪色遁形,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些朋友……好吧,他们拿我取乐,他们取笑我因为我总是戴着黄领带。后来他们就以为我真的喜欢黄色,虽然黄色确实过于花哨和张扬。我就说:“是的,对你们来说是这样,但对我可不是这回事,因为这是我能看到的唯一颜色。事实如此!”我生活在一个灰色世界中,就像黑白片时代的银幕世界,但黄色却能跳脱而出。这也许能说明[我的文字中为什么常出现黄色]。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讲过的一个笑话:他的一个朋友系了条领带,上面有黄色、红色,还有其他颜色;王尔德就说道:哦,老兄,只有聋子才会系这么条领带!
《巴黎评论》:王尔德说的或许就是我现在正系着的这条黄领带!
博尔赫斯:哦,就算吧。我记得曾把这个笑话讲给一位女士听,但她完全不得要领。她回应道:“当然了,这个人肯定是聋了,所以他才听不到人们怎么奚落他的领带。”这样的回答大概也能让王尔德捧腹,是不是?
《巴黎评论》:我倒是真想听听王尔德是如何作答。
博尔赫斯:当然了,谁都想听。我从没听过这样绝好的例子,一件事竟被如此完美地误解。完美得愚不可及!当然,王尔德的话是对某个概念的机智诙谐的翻译:在西班牙语和英语中,我们都有这么个说法,“响亮的色彩”或“吵闹的色彩”。这固然是个普通的词组,不过文学中所讲的其实也总是同样的东西。重要的是表述和言说的方式;比如说,采用隐喻表达。我年轻的时候总是尽力寻求新奇的隐喻,然后发现真正好的隐喻总是同样的。我是说,你把时间比喻成漫漫长路,把死亡比喻为沉睡,把生活说成是做梦;这都是文学中一些伟大的隐喻,因为对应着人世间的根本问题和基本要素。如果你编造出新的隐喻,可能有那么短暂的一瞬,它们会显得新颖奇特,但不会激发任何深层情绪。如果你觉得人生如梦,那确实是一种想法或念头,但这个念头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大部分人都必定会有的一种感受,不是吗?一种“常常会想到,但从未得到如此恰切表达”的念头。我想这些[经典隐喻]要比憋着劲去耸人听闻的更好,比特意去寻找那些以前从未被相互关联过的事物之间的关联要好;没有真正关联的事物被组合起来,那整个事情就像是一种杂耍、变戏法的花招。

《巴黎评论》:只是文字的杂耍?
博尔赫斯:只是文字花招而已。我甚至不愿把它们叫做真正的隐喻,因为一个真正的隐喻中,[本体和喻体的]两个概念是真正关联在一起的。但我也发现了一个例外——一个奇异、新鲜、漂亮的隐喻,出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诗歌。古英语诗歌中,战斗被说成是“刀剑的演出”或“长矛的对抗”;而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中,并且,我想在凯尔特语诗歌中也一样,战斗被说成是一张“人之罗网”。这很奇特,不是吗?因为说到网,其中还应该有着图案样式,用人编织而成,西班牙语的说法就是“一种丝线纤维”。我猜在古代战役中,确实可以看到某种形式的网:交战双方以长剑和矛枪对峙,在各自的阵地上排列交叉——诸如此类的形态。所以我想这里就有了一个新隐喻。当然了,感觉挺阴森恐怖的,像噩梦,不是吗?想想看,用活人,用有生命的东西结成一张网,而且还要有网的样式,网的图案。这个概念挺诡异,对吧?
《巴黎评论》:大致来说,这跟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用过的隐喻相对应:社会是一张网,谁都无法抽开其中一根线绳而不触动到所有其他的编结线。
博尔赫斯:是谁提过这个?
《巴黎评论》: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里。
博尔赫斯:哦,《米德尔马契》!是的,没错!你是说整个宇宙关联在一起,每样东西都关联着。这也正是斯多噶派哲学家相信预兆的原因之一。德·昆西写过一篇文章,很有趣的文章,正如他所有的文章那样妙趣横生;这个文章讲的是现代迷信,其中他提到了斯多噶派的理论。那个意思是说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体,是个活物,所以那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之间也有着姻亲般的关系。比如说,如果十三个人同桌吃饭,那一年之内其中一个人必定会死掉。这不仅是因为耶稣基督和“最后的晚餐”的典故,而且是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关联绑定在一起的。德·昆西说——我不记得那句话具体怎么说的了——世界上每一样事物都是一面秘密的镜子,是宇宙的映像。
《巴黎评论》:你经常提到那些给你带来影响的人,比如德·昆西……
博尔赫斯:是的,德·昆西对我影响巨大,还有叔本华的德语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是卡莱尔——说一下,我对卡莱尔还是相当反感的,我认为他是纳粹主义之类概念的发明人,是这类东西的策源地之一或者是始祖之一;不过,是卡莱尔把我引向了德语学习。然后我试着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当然了,跟大多数人一样,我读不下去,一筹莫展——大多数德国人其实也如此。然后我就说:“好的,算了吧,我来试试读德国人的诗歌;诗歌嘛,因为要控制篇幅,怎么着也会短得多。”我找了一本海涅的《抒情的间奏》,还有一本英德词典,就看起来;结果第二个或第三个月底,我发现自己不用再翻词典也能挺自如地读下去了。我记得自己完整通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是一本苏格兰小说,叫做《有绿色百叶窗的房子》。
《巴黎评论》:读这个小说时你多大?
博尔赫斯:我肯定是大约——当时书里还有很多地方我读不懂——我肯定是大约十到十一岁吧。当然了,在那之前,我已经读过[吉卜林的]《丛林之书》,还读过史蒂文森的《金银岛》——那是本很棒的书。但第一部真正的小说就是前面才说过的那个。我读的时候,就很想当个苏格兰人;
《巴黎评论》:你对英语文学的兴趣如此长久,而且你是如此热爱英语……
博尔赫斯:还是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吧:我是在跟一个美国人谈话。有一本书我必须讲一讲,而且是毫不意外的,那就是《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我完全不喜欢汤姆·索耶。我认为汤姆·索耶的出场毁掉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最后几章。瞧瞧那些愚不可及的笑话,都是些无谓的笑料;我猜测大概是马克·吐温认为他必须表现得有趣,责无旁贷,即使他并无玩笑幽默的心情,但还是要通过某种办法把这些笑料加入作品。根据乔治·摩尔的说法,英语国家的人总是这样想:“再糟的笑话也好过没笑料。”我认为马克·吐温是真正伟大的作家之一,但我猜他自己对这一事实几乎全无感觉。也许,为了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你必须对这样的事实不以为意。你可以埋头苦干、勤奋写作,将文中用到的每个形容词都斟酌再三,甚至一一尝试替换;但如果你能避免一些错误,那你就有可能写得更好。我记得萧伯纳说过,关于风格,一个作家确信自己能达到什么风格,那便是他所能有的风格,不会有更多可能。萧伯纳认为那种可把风格视为随意游戏的念头是相当荒谬,相当无意义的。举例来说,他认为班扬是个伟大的作家,因为班扬对自己所说的话抱有确定的信念。如果一个写作者对自己所写的东西都不能信任,那也根本不能指望读者会相信他的作品。
《巴黎评论》:也就是说戴上作家的“帽子”摆出写作的伪姿态?
博尔赫斯:是的,戴上作家的“帽子”,酝酿出恰当的情绪,然后写作。写完了,再投靠到现世政治的庸俗怀抱。
《巴黎评论》:你写小说时,修改很多吗?
博尔赫斯:最初的时候修改的。然后我发现当一个人达到一定的岁数,他会找到自己真正的调子。如今,写完的东西放了两周左右之后,我会争取再过一遍;当然了,总是有很多笔误和无意重复要避免,某些个人喜好的文字花招要注意不能玩得过火。不过,我想我现在写的东西总是能保持某一特定的水准——我无法再提高很多,但也不至于会写砸了。因此,我就任其自然,干脆就完全忘掉已经写好的文字,只去考虑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我此前最后写过的东西是《米隆加集》,意思是通俗歌曲。
《巴黎评论》:哦,我看过其中一辑;书印得很漂亮。
博尔赫斯:是的,那本《为六弦琴而写》,当然了,是指吉他。我小的时候,吉他是种很流行的乐器。那时,在几乎每个城镇的每个街角,你都可以看到有人拨弄吉他,虽然或许并不太熟练。有些最好的探戈舞曲是那些既不能写下曲谱也不识谱的人创作的,这些人灵魂中有音乐——好像莎士比亚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们就把曲调哼唱给别人听:曲子在钢琴上弹出来,然后被记下来,写在纸上,再出版,大量印出来给识字识谱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