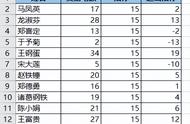《巴黎评论》:《自选集》内容遴选的原则是什么?
博尔赫斯:我的挑选原则很简单,就是入选的东西要比淘汰出去的让我感觉更好。当然了,如果我能更聪明点,我应该坚持把那些小说也剔除在《自选集》之外;然后在我死后,也许有人会发现被剔除在外的东西才真的好。这样做,或许更聪明,不是吗?我意思是说,只把薄弱平庸点的东西印出来,然后让某人来发现我把真货色遗漏在外了。
《巴黎评论》:他们(评论者)似乎很少意识到你的有些作品很有趣。
博尔赫斯:那些作品本来就打算逗趣的。现在有一本书要出来了,叫《布斯托·多梅柯的编年史》,是与阿道尔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合写的。书里写到了建筑师、诗人、小说家、雕塑家,诸如此类的。所有这些角色全是虚构的,而且都很贴近这个时代,非常有当代感;我们仅仅是尽量发挥,这件事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哪里。比如说,这里的很多作家对我说:“我们想了解你文字的寓意、内在的讯息。”告诉你吧,我们根本没什么内在讯息。我写作的时候,我写只是相当于有一件事必须要去做。我认为写作者不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搅和干预得太多。他应该让作品自己往下写,不是吗?
《巴黎评论》:你说过写作者永远不要被自己的理念裁判和操纵。
博尔赫斯:是的,不要。我认为理念不重要。
《巴黎评论》:那么,该用什么来裁判和评价写作者?
博尔赫斯:应该用他所能提供的乐趣和读者所能体会到的情绪感受来评判。至于理念,一个写作者有没有什么政治观点或者别的主张毕竟不是很重要的事,因为一部作品将会无视这些理念而存在下去。
《巴黎评论》:读者经常把你的小说称作寓言。你喜欢这种说法或描述吗?
博尔赫斯:不,不喜欢。这些小说没打算写成寓言。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它们是寓言……就是说,如果它们是寓言,那它们是恰巧成为寓言,但我的意图从来不是去写寓言。
《巴黎评论》:像卡夫卡那样的寓言,也不是吗?
博尔赫斯:说到卡夫卡,我们了解得极少。我们只知道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不满。当然,当他嘱咐朋友马克斯·布罗德,要后者把他的所有文稿都烧掉——诗人维吉尔也说过这样的意愿,我猜测卡夫卡也知道布罗德不会那么做。如果一个人想毁掉自己的作品,他把作品扔到火中,那样就结束了一切。当他对自己的亲密友人说:“我要你把我那些文稿销毁”,他知道朋友永远也不会照办;而这个朋友也明白他嘱托人知道,而他知道另一个人知道他知道……如此循环不已。
《巴黎评论》:听起来非常的亨利·詹姆斯化。
博尔赫斯:是的,确实如此。我想,我们可以用一种远为复杂的方式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发现卡夫卡的整个世界。我猜这两个人都认为世界是复杂的,同时也是无意义的。
《巴黎评论》:无意义吗?
博尔赫斯:你认为不是这样?
《巴黎评论》:不,我并不真这样想。拿詹姆斯来说……
博尔赫斯:拿詹姆斯来说,好吧。在詹姆斯那里,是这样的。我不觉得他认为这个世界有任何的道德目标或追求。我猜他也不信上帝。我想,实际上他给兄长,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写过一封信;在信里他说到世界是个钻石博物馆。我们不妨说这个博物馆是个畸人怪事大集合,不是吗?我猜亨利·詹姆斯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而说到卡夫卡,我认为卡夫卡在寻找什么东西。
《巴黎评论》:寻找某种意义?
博尔赫斯:某种意义,是的;但没找到,或许。我认为他们都生活在某种迷宫中,你说呢?
《巴黎评论》:我愿意赞同你的说法。比如说像《圣泉》那样的书说的就是这个。
博尔赫斯:对的,《圣泉》,还有很多短篇小说。
《巴黎评论》:你会不会说,你自己的短篇中,起始点也是一个情境,而不是一个人物?
博尔赫斯:在一个情境中,没错。但那些围绕勇猛这一理念的篇章除外;勇猛、好勇斗狠,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主题。英勇勇猛,对的,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不很勇敢。
《巴黎评论》:就是因为这个,你的短篇中才有那么多的刀啊、剑啊,还有枪?
博尔赫斯:是的,可能吧。
《巴黎评论》:用刀使得这种行为的发生方式显得更古老?
博尔赫斯:是的,一种更古老的形式。而且,用刀体现了一种更个人化的勇气理念;因为你可以是个神枪手,但未必很勇猛;但如果你是与对手近距离格斗,双方手拿刀子……就是很具体的勇气...贫民区有些专门的词——或者说这些词当中的一个——来指这种刀子,一个就是elfierro/钢刀;不过当然了,这个词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但其中一个称法——很遗憾这个词已经几乎失传了——叫做elvaivén/挥动、甩动,意思是“快速来回闪动”。这个词(一边做出手势动作)让你看到刀子的闪烁光亮,突然的闪耀。
《巴黎评论》:那刀鞘就像枪手的枪套?
博尔赫斯:的确,是的,就像枪套——装在身子左侧。在转瞬之间拔出刀子,你就能完成一次“闪动”攻击。这个elvaivén是当成一个词来拼写的,大家都知道它指的就是刀子。而elfierro就是个相当没劲的名字,因为把刀叫做“钢”或者“铁”完全没什么味道,但elvaivén就很有神韵。
《巴黎评论》:有两个作家,就是乔伊斯和T.S.艾略特,我想问问你的看法。你是乔伊斯最早的读者之一,甚至还把《尤利西斯》部分地翻译成了西班牙文,是吗?
博尔赫斯:是的,不过,我只翻译了《尤利西斯》的最后几页;我的翻译恐怕错误百出。至于艾略特,一开始我认为他是个更好的评论家,好过他作为诗人的表现;现在,我想他有时候是个很高妙的诗人,但我发现,作为一个评论家,他过度习惯于划清一些微妙的界线,而且总是如此。如果你以一个伟大的批评家为例,比方说爱默生或者柯勒律治,你会感觉他确实已经读过一个作者的作品,他的评论来自他对这个读者的切身感受;而在艾略特那里,你总是会想——至少我总是感觉到——他只是在对某位教授的观点表示同意或者对另一位的见解表示略有保留或反对。因此,艾略特的评论没有创造性的新东西。他是个聪明人,会划清一些微妙界线,我想他的做法也没错;但同时,读过另外的评论后,举个现成的例子来说,柯勒律治评莎士比亚,尤其是对哈姆雷特这个角色的评价,你会发现柯勒律治为你创造了一个新的哈姆雷特;再比如读过爱默生对蒙田或者其他任何作家的评论后也会有新发现。但在艾略特这里,就没有这样的创造行为。你会觉得关于某个主题,他是读了很多书,但他只表示同意或者反对——有时候还做出些稍微有点刻毒难听的评价,不是吗?
《巴黎评论》:确实是,不过后来他又收回了那些话。
博尔赫斯:是的是的,他后来收回了。当然了,他收回那些话是因为在那时他一开始可能被人扣上了什么帽子,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愤青”。最后最根本的,我猜他把自己当成是英语文学的经典大家,然后他发现自己必须对同行大家礼貌尊重,所以后来就把以前说过的大部分话收回——他那些话说到了米尔顿,甚至还批过莎士比亚。不管如何,他毕竟可能会从一个自我理想化的角度去看,觉得他与那些经典大家都属于同一个学术和文艺队列。
《巴黎评论》:艾略特的作品,主要是他的诗歌,对你自己的写作有过什么影响吗?
博尔赫斯:没有,我不认为有影响。
《巴黎评论》:但《荒原》与你的小说《永生》之间有些特定的相似之处,给我印象挺深的。
博尔赫斯:好吧,可能会有点什么吧,但就此而言我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注意到,因为我喜欢的诗人中不包括他。济慈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会比艾略特高许多。实际上,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我认为弗罗斯特也是个比艾略特高明得多的诗人。我的意思是,一个更优良更好的诗人。不过,我猜艾略特非常聪明,比前二者聪明得多;但是,智力与诗歌没多大关系。诗歌发源于某种更深层的东西,超出智力的边界范围。诗歌甚至与智慧都没有关联。诗歌是它自身的东西,有它自己的天然本质;无法定义。我记得——当然,是在我年轻时——当艾略特对桑德堡表示不屑和轻蔑,我甚至为此愤怒。我记得他这样说的——我不是在照搬原话,而是转述他的主旨;他说古典风格很好,因为古典风格可以让我们去解决诸如卡尔·桑德堡先—生之类的写作者。把一个诗人称作“先—生”(笑),这个词透露出说话者傲慢自大的心态;
《巴黎评论》:那么,你欣赏桑德堡?
博尔赫斯:是的,我欣赏。当然了,我认为惠特曼比桑德堡重要得多,但当你读惠特曼,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文学之人,也许是个不那么博学多识的文人;是这么个文人在尽其所能地用口语方言,在尽量多地使用俚俗语言写作。而在桑德堡笔下,俗言俚语看上去是自然到来的。当然了,我们实际上有两个桑德堡:一个是剽悍的、粗糙的桑德堡,另一个则是很雅致精巧的桑德堡——尤其是在他那些处理自然风景的清新小诗中。举例来说,他有时候描绘雨雾,会让人联想起中国水墨山水。而在桑德堡的另一些诗作中,你则会想起黑帮啊、街头混混啊,这一类的流氓人物。但我以为他可以两方面兼顾,而且我认为他在这两方面同样真实诚恳:一方面他力尽所能去做他的芝加哥主题诗人,同时他又能以截然不同的情绪心态去写另一种诗行。关于桑德堡,我发现另一个奇特的地方是,首先是惠特曼——当然,惠特曼是桑德堡的前辈先行者——惠特曼的笔下充满了面对未来的希望;而桑德堡的写作,他写的时候似乎已经置身于将来的两三个世纪。当他写到美国[向西部]探险开拓的力量洪流,或者当他写到工业帝国的扩张,写到当时的战争以及其他等等时,他笔下给人的感觉是,仿佛所有那些事情都早已发生,他是在回顾。
《巴黎评论》: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幻梦元素,这也触发了我的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对“奇异”的见解。这个词,你在自己的写作中用得也非常多;我记得,比如说,你把《绿色宅邸》称作一部奇异的小说。
博尔赫斯:是啊,是这样。
《巴黎评论》:那么,你愿意如何定义奇异?
博尔赫斯:我在想,我们能否定义这个词。我以为,这更多是作者心中的一个意愿。我记得约瑟夫·康拉德——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想这句话是在某本书的前言中,那书好像是《暗之线》,但好像又不是,是……
《巴黎评论》:是《阴影线》吗?
博尔赫斯:是的,《阴影线》。在前言中,康拉德说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很奇异,是因为有个船长的鬼魂让船静止在大海深处。他写道——他的话对我冲击挺大,因为我也矢志写匪夷所思的奇异故事——特意去写一个奇异的故事并不是要觉得整个宇宙都是奇异和不可思议的,也不是说,一个人坐下来,有意去写点奇异的东西,就必然要抛弃常识、感受力和辨识力。康拉德认为,当一个人去写作,即使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写他身边的世界,他也是在写一个奇异的故事,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奇异的、神秘莫测的、不可理解的。
《巴黎评论》:这些年,你经常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合作,是吗?
博尔赫斯:是的,我总是跟他合作。每天晚上,我在他家吃晚餐,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写东西。
《巴黎评论》: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是怎么合作的?
博尔赫斯:好吧,不过情形说起来相当怪异。当我们一起写,当我们合作时,我们把自己叫做“H.布斯托·多梅柯二人组”。布斯托是我的一个高祖父,多梅柯是他的一个高祖父。你看,怪异之处是当我们写作时,我们写的大多是滑稽幽默的东西——即使是悲剧故事,也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讲出来,或者说讲的时候,仿佛讲述者几乎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我们一起写的时候,我们写出的东西,如果是成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成功的,干吗不能成功?还有,我在说的时候用的是复数,我们,不是吗?当我们的写作成功,结果出来的东西跟卡萨雷斯的就大不相同,跟我的也相差甚远,甚至连那些笑话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创造出来一个介于我和卡萨雷斯之间的第三人;我们不知怎么搞的就弄出了一个第三者,跟我和他都差异挺大。
《巴黎评论》:一个奇异的作者?
博尔赫斯:是的,一个奇异的作者,有他自己的好恶,还有一种就是要显得荒谬乖异的个人风格;但是他自己的风格,跟我自己想创造一个乖谬角色时所用到的那种风格大不相同。我想,这就是合作时唯一可行的方式。一般来说,我们先是一起把情节过一遍,然后开始动笔——其实,我这里应该说动打字机,因为卡萨雷斯有台打字机。我们开始写之前,先讨论整个故事,然后检查细节;当然,我们也会改动这些元素:比如,我们想出一个开头,但后来又可能想到开头也可以充当结局,或者会想到,如果某个人物什么也不说或说了什么无厘头的话,效果或许更惊人。故事定稿之后,如果你问我们,某个形容词啊或者某个特定的句子是比奥伊写的还是出自我的手笔,我们就答不上来了。
《巴黎评论》:是来自那个第三者。
博尔赫斯:是的。我想这是合作的唯一办法,因为我之前也试着与其他人合作过。有时候合作进展得不错,结果很好,但有时候其中一人会觉得对方是来跟他竞争的。或者,如果不是竞争,就拿我跟贝鲁的合作为例,我们开始合写,但他羞怯而且很谦逊,是那种非常礼貌的人,因此,如果他说了什么,而你又表示了一点异议,他就会觉得受了打击,就收回自己的意见。他会说:“噢,是的,当然了,当然,对的。是我完全搞错了,是个大错误。”或者,如果你提议什么,他会说:“哦,那很棒!”这样合作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而在我和卡萨雷斯这里,我们不觉得彼此好像是两个竞争者,或者说,也不会感觉我们两个人是在下棋,在相互博弈。没有谁胜谁输的概念。我们所考虑的是故事本身,作品内容本身。
《巴黎评论》:你说过,你自己的作品已从早期的表现表达转变为后期的暗示,或说隐喻?
博尔赫斯:是的。
《巴黎评论》:那么,暗示,你指的是什么?
博尔赫斯:是这样的,我意思是说这个:当我开始写作,我认为一切都应该由作者定义。那时我认为所有东西必须由作者定义,任何普通的惯用措辞都不应该用在作品中。不过,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写作者会觉得他的意思和想法,无论是好是坏,应该简单朴素地表达出来,因为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必须试着把你的想法或者那种感觉或那种情绪传达到读者的意念中。
《巴黎评论》:那么,你的努力方向就是一种经典的文字风格?
博尔赫斯:没错,我现在是尽力这样去做。一旦我发现有格格不入的词,我就把这个词剔除,换上一个普通的常用词。我记得史蒂文森这样说过,在一页写得很好的文字中,所有的词看上去都应该是同样的感觉。如果你写下一个粗鄙的词,一个惊悚突兀的词或者一个古色古香的词,那么篇章的规则和统一性就打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读者的注意力就被这个词分散了。即使你写的是形而上的玄学论述,或是哲学,或者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也应该让别人读起来感到流畅才行。
《巴黎评论》:约翰生博士也说过类似的话。
博尔赫斯:是的,他肯定说过;不管怎么说,他肯定也同意这种说法。你看,他自己的英文相当累赘;你的第一感觉是他是在用一种累赘笨重的英文写作——有太多的拉丁语词汇在里面——但如果你再读读他已经写完的东西,你会发现,在那些交错纠缠的词语背后,总是有着一个含义,而且一般来说总是一个有趣的、全新的含义。
《巴黎评论》:一个个人化的内在含义吗?
博尔赫斯:是的,个人化的。因此,即使他是以拉丁文风格写作,我还是认为他是所有作家中最能体现英语风骨的。我认为他是——我这里大概要亵渎神明,对前人不恭了;不过当然了,既然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干吗就不能亵渎神圣?——我认为约翰生远远比莎士比亚更能代表英语文字的特质。这是因为,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是英国人最典型的特质,那就是他们那种有保留的、不把话说满的表述方式。而在莎士比亚这里,没有什么有保留的和有节制的陈述;反倒是完全相反,他过分渲染、夸大其辞——我想好像有美国人这样说过。我认为约翰生,他写的是一种拉丁文风格的英文,此外还有华兹华斯——他写作用到更多的撒克逊古英语词汇——另外,还有第三个作家,他的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噢,这样吧,让我们就说约翰生、华兹华斯,还有吉卜林,我认为他们三个都远远比莎士比亚更能体现英语的典型风骨。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总觉得莎士比亚那里有些意大利人的做派,有些犹太人的东西;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人才钦慕赞赏莎士比亚吧,正是由于莎士比亚跟他们是如此不同。
《巴黎评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是法国人讨厌莎士比亚的原因吧;因为他夸大其辞。
博尔赫斯:他就是相当地夸大其辞。我记得看过一部电影——那已经有些天数了,影片也不是很精彩——叫做《亲爱的》。那里面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句。那些诗句被引用时总要好一些比在原作中好一些,因为他是在以这些诗行定义和指称英国;他把英国称作,比如说“这另一个伊甸,一半的天堂……这嵌在银海中的宝石”,还有如此等等;最后莎士比亚还说了这样的话,“这个王国,如斯之英国。”在引用的情形下,观众听到这里也就算了,即刻终止,但在原文文本中,我想这些诗句还要继续下去,以至于味道和意义尽失。真正的意义要点本来是说一个人试图去定义他的国度英格兰,他是如此热爱这个王国,发现自己最终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直接感叹一声“哦,英格兰”——就像你会感叹“哦,美国”。但如果他说“这个王国,这方土地,如斯之英格兰”,然后还继续说什么“这半个天堂”之类的,那全部意味就会流失,因为英格兰应该就已是最后一个词。好吧,我猜想莎士比亚写作总是很匆忙——处于打拼期、身为演员的莎士比亚曾向本·琼生说过此事,所以大概就是那样吧。他没时间停下来感觉一下,英格兰这个词就已经足以概括一切,可以把其他一切排除掉,应该是最后一个词了;此时他实际上可以对自己说:“好吧,我已经尝试了,但不可能再做什么发挥了。”但莎士比亚在这里没停步,而是继续他的暗喻修辞和高调渲染,因为他已经惯于夸大其辞。即使在“此外,仅余沉寂”这样一句著名台词中——我想那是哈姆雷特的临终遗言吧——也不例外。这句话显得有些虚假矫饰,故意去强化留给观众的印象。我想谁都不会在临终时这么说话的。

博尔赫斯与第二任妻子
《巴黎评论》:根据这部戏的情境,《哈姆雷特》中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出现在克劳狄斯祷告的那一幕之后,哈姆雷特走进母亲的房间,说道:“哦,母亲,有什么事吗?”
博尔赫斯:“有什么事吗?”正好与“此外,仅余沉寂”相反。至少在我看来,“此外,仅余沉寂”有种空洞虚假感。人们会觉得莎士比亚是在这样想:“那么,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就要死了,现在怎么办?他一定要说点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所以他处心积虑写出了这一句“此外,仅余沉寂”。现在可能是让人印象深了,但却虚假做作!他是在以诗人的身份去升华发挥,却没有把哈姆雷特当作一个真实人物,从这个丹麦青年的角度去考虑。
《巴黎评论》:你写作时,会设想自己在为哪一类读者而写,假如你确实这么设想的话?什么样的人是你的理想读者?
博尔赫斯:也许只是我的几个私人朋友。不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从来不去读自己已经写完的东西。我恐怕会为自己所写的文字而感到羞愧,我很怕去读旧作。
《巴黎评论》:很多人读你的作品,你指望许多读者能理解其中的暗示和讽喻指涉吗?
博尔赫斯:没这样指望。大部分的暗示和指涉放在作品中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人的玩笑。
《巴黎评论》:私人玩笑?
博尔赫斯:是那种不指望与别人分享的玩笑。我意思是,如果读者也理解,那当然更好;但如果读者不理解,我也毫不在意。
《巴黎评论》:那么,你的手法和意图与其他人作品中的暗示反差很大,比如说艾略特的《荒原》。
博尔赫斯:我认为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想让他们的读者感到困惑茫然,然后再绞尽脑汁去理解他们的意思。
《巴黎评论》:看起来,你读过的非虚构或纪实作品大概与小说诗歌之类的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是这样吗?比如说,很显然的,你喜欢看百科全书。
博尔赫斯:哦,确实。我非常喜欢百科全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来这个图书馆看书。我那时很年轻,也很害羞,都没有胆量跟人家说要借哪本书。那时候,我也很,我不想说我很穷,但那时候我确实也没两个钱——所以我就每天晚上来这里,拿起一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来看,那种老版本的。
《巴黎评论》:有些读者觉得你的故事冷漠、不近人情,挺像更年轻一代法国作家中的一些人。那是你的本意吗?
博尔赫斯:不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那完全是因为我太笨拙吧。因为我对笔下的人物感触很深。我对他们的感受是如此之深,所以我才讲他们的故事,所以我用那些陌生奇异的表达符号来写故事,为的是让读者不至于会发现那些故事全都多多少少带有自传的色彩。那些故事跟我有关联,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我猜,那是一种英国人式的内敛,不是吗?
《巴黎评论》:那么,像那本叫做《永恒性》的小册子之类的,对于要读你作品的读者来说,就是一本好参考书喽?
博尔赫斯:我想是吧。此外,写了那本小书的女士是我的一个密友。我是在《罗杰氏分类辞典》中看到[everness]这个词的。然后我想到这个词是约翰·威尔金斯主教发明的;他发明了一种人工语言。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写过这个。
博尔赫斯:是的,我写过威尔金斯。他还造过一个很精彩的词,但很奇怪的是,至今都没有哪个英语诗人用过;那是一个精彩到恐怖的词,真的,一个可怕的词。当然了,everness比eternity/“永世”要好,因为eternity如今已经用俗用滥了。Everness也比德语中的同义词Ewigkeit好得多。但威尔金斯还造过一个漂亮的词,一个仅凭它自身便构成一首诗的词,充满了无助、悲怆和绝望;那就是neverness。一个漂亮[到冷酷]的词,不是吗?他发明了这个词,但我不明白诗人们为什么任由这个词荒废着却从来不曾用过。
《巴黎评论》:那你用过吗?
博尔赫斯:不不,从来没有。我用过everness,但neverness可真漂亮。其中有一种无助无望感,不是吗?任何其他语言中,或者包括英语在内,都没有一个词能有着同样的意义。你或许会说“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但相较于以ness结尾的这个撒克逊单词neverness,就非常柔和平淡了。济慈用过nothingness这个词,写道:“直到情爱与名望沉入虚空/Tillloveandfame tonothingnessdosink”;但nothingness/虚空,我觉得,比neverness的冲击要弱。西班牙语中有nadería/“琐屑、虚空”这个词以及很多相似的近义词,但没有一个能对应neverness。所以,假如你是个诗人,你就应该用这个词。遗憾的是,现在的辞典中也不收录这个词。我不认为这个词曾经有人用过。或者也许有哪个神学家用过;这是有可能的。我猜乔纳森·爱德华兹可能会喜欢使用这一类词,或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也会;当然了,莎士比亚也可能,因为他非常热衷词语游戏。
《巴黎评论》:还是暂时回到你自己的作品:我常常好奇,你的作品是如何安排进那些不同的集子的。很明显,写作年代顺序不是安排的原则。是不是根据主题的相似性来编选?
博尔赫斯:不,不是按写作年代。有时候同样的一个寓言或者故事,我发现自己已经写了两次,或者发现两个不同的故事有着同样的寓意,我就决定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这就是唯一的编选原则。因为,比如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写了一首诗,一首不太好的诗,在多年以后又来重写;重写完了之后,我的某些朋友告诉我:“哦,这跟你大约五年前发表的那首诗是一样的。”我就说:“哦,事实上就是同一首啊!”但我一点儿都不认为它们是完全一样的。我认为,毕竟,一个诗人可能只有五或六首诗可写,不会再多。他所有其他的诗歌都是相当于从不同的角度来重写那几首,在不同的年代也许会换成不同的情节和不同的人物主体,但这些诗在本质上和内在核心方面还是那同样的几首。
《巴黎评论》:你也写过很多评论和杂志文章。
博尔赫斯:对的,我必须要写那些。
《巴黎评论》:你只挑自己想评论的书去写书评吗?
博尔赫斯:是的,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巴黎评论》:所以你的选择真正表明了你的趣味?
博尔赫斯:哦,是的是的。比如,有人叫我去写什么“文学史”的书评,我发现其中很多滑稽可笑的明显错误,而作者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诗人,于是我就说:“不行,我不想写这个书评了,因为如果我要写的话,就会说些反对的意见。”我不想攻击别人,尤其是现在;我年轻时,是的,那时我曾很喜欢批别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攻击别人是很徒劳的举动。你写文章赞同或者反对别人,那既不会帮到他,也不会伤到他。我想一个人可以得到提升,从他自己的写作中得到提升——无论是被他自己的作品激励还是打击,而不是从别人对他的评价中得到帮助;所以即使你大肆自吹自擂,而且别人也夸你是天才,但你最终会露出原形。
...
(杨凌峰 译)
《巴黎评论》第五十一期,一九七一年春季号
本文由中国诗歌网综合整理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