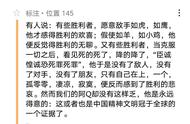阿Q就是这样,他永远做个“胜利者”,挨了打之后又从小尼姑那找补回来,不觉是欺软怕硬,反而沾沾自喜。
可摸过小尼姑光滑不已脸蛋的阿Q感觉自己手上约莫不对劲,竟比平时滑腻些,又想起小尼姑气愤不已的骂话“断子绝孙的阿Q”,阿Q有些浮想翩翩了。
所以在吴妈正与阿Q闲聊时,阿Q竟突然冒出来一句“我和你困觉”,还激动不已地对着吴妈跪了下去。
吴妈愣了一下,惊吓不已地跑出去,带着哭腔地嚷嚷,这回大家都听见了,赵太爷还直接拿了个大竹竿来撵阿Q。
这下子,阿Q在未庄是真无立足之地了。
吴妈是赵太爷家唯一女仆,阿Q来赵太爷家做短工,竟对吴妈有龌龊想法,哪个正经未庄人会租用阿Q呢?何况阿Q所有财产都被赵太爷收走了。
于是人憎狗嫌的阿Q只能进城另谋出路。
等阿Q再回到未庄,已大不相同。
穿得是新夹袄,兜里有好些钱,还带回来好些衣服,都说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会未庄人都对阿Q敬畏不已。
阿Q也不含糊,在酒店、茶馆、庙檐下,絮絮叨叨地讲起他在城里的辉煌经历。
在举人老爷家打工,回来是不满城里人精致的做派,还观看了一场革命党被*头的大场面。
阿Q讲起这些昂首挺胸,眼里满是神气。

这下子连未庄之前那些对他避如蛇蝎的女人们也都对阿Q和善起来,阿Q自然飘飘然了,对赵太爷的态度也不如之前恭敬了。
赵太爷想从阿Q那里买衣服,阿Q嘴上答应下来,却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这副不上心的模样让赵太爷有些气愤,对其他人便说:阿Q的东西怕是有古怪。
未庄最大户赵太爷积威已久,他的话如同“圣旨”一般,未庄人便渐渐对阿Q敬而远之了。
阿Q不以为意,还继续对着一帮闲人吹嘘自己。
讲起自己其实是帮小偷打下手的,那日自己刚接过从墙里扔过来的包,就听见里面闹了起来,以为事情败露,就赶紧跑路了。
自己带回来的东西正是别个小偷偷的,自己可算是不损一份就得所有了。
可阿Q引以为傲的事情在未庄人眼里不值一提,觉得阿Q竟连小偷都被资格做,就是当最低等人的料,更是看不上了。
阿Q不料自己又遭人嘲笑,见别人讲起革命党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想起自己看过革命党被*头,一回又喝得醉醺醺的,竟装作革命党大声嚷嚷“造反了!造反了!”
见未庄人被惊吓不已,阿Q心里便痛快了。
其实对于革命党,阿Q是一点不懂。
见革命党被*头,就以为他们是干造反的,毕竟在阿Q心里只有造反的人才会被*头,但是造反的人又怎么样?能让人怕就行。

一天夜里,赵太爷家遭了抢劫。
阿Q本就爱看热闹,就提着胆子远远观望,看一群人络绎不绝地从赵太爷家搬东西出来,眼馋不已。
这或许就是要“造反”的革命党*好事,可是人家不让自己加入,搬财物这等好活也沦不着自己,这革命党迟早要完蛋,迟早要被拉到城里被*头。
阿Q愤恨地想着,这其实也是典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吧。
可是未料到,阿Q竟能和这件事扯上关系。
睡得好好的阿Q是半夜被人从土谷祠抓走了,随即被送上了衙门大堂审问。
阿Q见高堂上坐着个上了年纪的老爷,两旁站些穿长衫的人物,下面又站了一排兵,皆对他怒目而视。
从未见过这场面的阿Q不由弯了膝盖跪了下去,他甚至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被抓了。
那些长衫人物都让阿Q站着回话,可阿Q就是站不起来,不如跪着,这不由让人骂一句“奴隶性”。
随后那高堂上的老爷就开始审问阿Q是否跟那晚抢劫赵太爷家的人有关?
说到这,阿Q愤愤不已,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想加入“革命”,却没人叫自己。
坐在高堂上的老爷便使了个眼色,就有人拿了一张纸让阿Q画押。
这是阿Q的手第一次跟笔和纸接触,更觉惶恐不已,人家让阿Q画一个圆吧,可阿Q的手抖个不停,尽管阿Q竭力要画个好圆,也控制不住颤抖的手,竟画成了个瓜子模样的。
这阿Q感到羞愧不已。
阿Q觉得人世约莫是要画个圆的,可自己连个圆都画不好,哪里还能见人?但想到”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又释然了。

或许正是这种心理,阿Q对于一大早被换上囚服抬上囚车也是泰然处之了。
人生天地间未免是要被*头的,未免是要被游街示众的。
可当阿Q看见吴妈出神地看着士兵背上的洋枪,听着周围叫”好“的喝彩声时,不免戚戚然地想起自己四年前遇见的一只饿狼,那眼神”又凶又怯“,闪闪如鬼火,不仅想啃食自己的骨肉,似乎还想撕咬自己的灵魂。
阿Q终于两眼发黑,”救命“一声是喊不出来了,等耳边听到嗡的一声枪响。
阿Q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