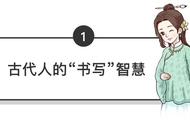《托米丽司女王》(Tomyris,2019)剧照。
我很小就读过这个故事,托米丽司女王复仇的凄美悲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当时用笔尖蘸血复仇,也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这位心目中的女英雄。但女王的复仇,可以载诸史册,成为流传千古的史诗,而我的复仇,得到的却是全班同学另类的眼光。我被欺凌是符合落后就要挨打的公理;他欺凌我,是顺应强者就要打人的定律,而我反抗,就是“脑子有病”;我复仇,就是“急了,疯了”。
当然,我还要被“请家长”。
当着我和他妈妈的面,我要和那位同学假意惺惺地互相道歉——老师大概觉得“互相道歉”这一点尤为显得她公平公正。在把那位同学和家长送走之后,老师单独把我和妈妈留在办公室里,批评我说:
“你是个好学生,怎么也和人打架?他将来毕业就进社会了,你是将来要考重点大学的人,你怎么能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呢?万一落个处分怎么办?”
是啊,我是所谓的“好学生”,好学生不仅意味着成绩优异,还意味着品德优良。而所谓的良好品德,最重要的莫过于听话顺从。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家听父母的话,在社会听有地位权威之人的话,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好人来说,这恐怕是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一课——学会如何顺从。
而当你受到委屈,遭遇不公时,你唯一的途径就是求庇于一个更高的权威恩赐公平给你——众所周知,公平永远都只能掌握在那些手握权柄之人手中,只有他们才有施舍公正的权力。而我,要想做个好人,唯一的职责就是顺从这一权威,我没有,也不该有自己通过反抗寻求公正的权利。就像老师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他打你,是他不对,你还手,就变成你不对了。”——或许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对一个学校,一个班级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学习环境。他打我,固然是他不对,但只要不是在学习环境中,其罪过就能减轻不小,因此,把我按在无人发觉的角落里打,证明他还挺顾全大局;我隐忍,没有把冲突放大,同样也是顾全大局,维护了学习环境的和谐稳定。但是,我反抗了,并且是在教室里反抗,便是破坏了和谐稳定的学习环境,我是和他一样的坏学生,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给整个班级丢了脸,就像老师批评的那样:
“你一个好学生,在班里当着这么多人面打架,你让别的班看见了怎么想!”
这就是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不是没有丑事,只是不可外扬,而为了不外扬,丑事只能当作没发生过——老师说得是对的,我确实不顾全大局,不仅破坏了自己好学生的形象,更给班集体的形象抹黑,我光想着自己的反抗复仇,却没有顾及集体的荣誉——在班级脸面这一更大的公平面前,个人微小的公正理应被牺牲。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哭了,但我那时还不懂得如此高深的道理,我只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太“自私”,不顾“集体”,但这不是我哭的真正原因。而是因为我看着妈妈手里提着的袋子里放着的那件T恤,那件欺负我的人穿着的T恤,那件被我甩上了复仇钢笔水的T恤,那件我真的“赔不起”的T恤。妈妈要把它带回家洗干净。
但是,我也是“帮凶”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当我把那只兔子举在半空中,向下摔时,我脑海里并没有想起鲁迅的这段话,我那时脑子里是麻木的,几乎一片空白,只有在学校里受了欺负的那种莫名的悲愤,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愤,一种孤独无助而又无所适从的感觉,在我眼中,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无法变强,就活该被打,我遵守这个法则是如此痛苦,但是不遵守这个法则去反抗,又会被这个世界所排斥。是啊,俗话是有“兔子急了还咬人”“狗急跳墙”这样的话,但无论是如何咬人,如何跳墙,终归也只是兔是狗,做不成人,我那时承认这种欺凌是合理的,虽然那些大人名义上说“打人不对”。但他们在教导“落后就要挨打”,在批评我们说“他打你他不对,你还手你不对”时,就已经把人牢牢钉在了这套矛盾而又合理的法则当中了。

微电影《沉默难鸣》。
所以在家里养的那只兔子身上,我要践行这一让我苦痛却又无可奈何的法则。这兔子本来就很可怜,只有一个破纸盒子栖身,吃我家做菜剥下来的烂菜叶子为食,因为住在四楼,所以几乎就没带它下楼去跑跳。它生在笼子里,长在阳台上,比我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的范围还要狭窄。
但它不会欺负我,不会反抗我,它的三瓣嘴伤不了我,哪怕是被它有力的后腿蹬一下儿,也只是软软拍了一下儿而已。于是我把它举起、松手,看着它像一团灰色的、毛茸茸的球一样落在地上。
我这样做了两次,不知为什么,我看着这只兔儿在地上伸开它原本因害怕蜷起的脚爪,在瓷砖上扑腾起身,鼻子快速地一耸一吸的样子,心中忽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快感,就像我真的把生死的绝对支配权握在手中一样——被支配者的无助与恐惧,是支配者贪婪的食粮,我也终于尝到了这个味道——
欺负人,就是这种感觉吗?
我第三次把兔子举起来,但当我把它举到眼前时,我看到了它的眼睛,黑色的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我看见了它的三瓣嘴里,洇出了鲜红的血痕,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它冰凉的脚爪蹬到我的胸口上,想挣扎着从我的魔爪中逃开,但却被我掐得死死的,无法逃脱,也无处可去。
它被堵到四角了。
我也一样。
我突然抱着兔子,跪在地上哭了。“对不起”,我重复着:“对不起”。我知道兔子听不懂我的道歉,但这句话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是现在的我,说给过去以及未来的我听的——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小恶魔”提利昂。
在班里,是有这样一个人,长相活脱脱就是《权力的游戏》中的“小恶魔”提利昂,不过他并非是侏儒,只是个头矮小,他总是龇着牙露出一脸笑,但那笑容中不是透着藏不住的阴损,就是露出遏制不住的谄媚。前者是给我们这样班里常受欺负的弱势,后者则是绽放给那些惯常欺负人的强者。以他的个头样貌,原本也很“讨打”,班里几乎没有喜欢他的人,但是,他似乎在挨了几次欺负后,就靠着如簧巧舌和谄媚功夫,抱上了那几个班里强人的大腿,走路也一时横了起来。他有时会大大咧咧从我桌上拿走作业抄,而我也对他听之任之,起码,他不会像他那几个靠山一样动手打我,但是,我不能违拗他的意愿,他会煽动那些家伙对我报以拳脚。
说来奇怪,尽管他从未和我动过手,但是,我对他的憎恶,却明显在那些动手欺负我的人之上。我憎恨他在强人旁边耀武扬威的样子,憎恨他不是凭实力而是凭谄媚靠山狐假虎威。有一件事虽然与我毫无关联,却至今让我记忆深刻。那是在学校运动会上,我看到一个欺负过我的家伙——也是年级的赛跑健将,从赛场上下来后,满身是汗地走到小恶魔的旁边,顺势一头枕在他的膝盖上。而这个家伙,就像苏丹王的宠妃一样,用毛巾给他擦拭头上和身上的汗水,以一种相当宠溺的姿态为他捋顺头发,按摩肩膀。而那个家伙就这样怡然自得地枕在他的膝盖上,仿佛他真是运动场上左拥右抱的王。
那一刻,我脑海里飘过的四字成语险些脱口而出:“狼狈为奸”。
在那之后,我明白了一个本不该明白的道理:不仅打人是种实力,谄媚有实力的人也是种实力。比起前者,后者抛弃的不止有善恶良知,还有自尊心。
在高三的那年,我其实并没有怎样被人欺负,而原因,是来了一个外地转校生。
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记得他的长相,他和我一般高,瘦瘦的,头发邋遢,浓浓黑黑的眉毛下是一双细长的眼睛,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薄薄的嘴唇总是抿起来,因此,看见他,就让人想起那个网红一时的悲伤蛙表情包,但每当见到同学,他总会露出一副微笑的神情,但却透着一种淡青色的阴郁。
他的校服只有周一是干净的,到了周五就脏脏的了,一个学期永远穿着一双脏兮兮的廉价白球鞋——我之所以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所有人都穿着校服,只有鞋子能区分出家庭境况。有钱人家的同学会穿一看就价格不菲的篮球鞋或是足球靴,而我这样家境一般的学生,一年到头穿的都是从大胡同批发市场买来的蓝色和灰色的帆布鞋,穿那种廉价白球鞋的同学,就只有他而已。
我骨子里是很有些势利的,但这种势利不是崇拜强权,而是我很看重学习成绩。我最好的朋友和我一样,都是班级前五名左右,我们互相帮助,也互相竞争,彼此都是成绩上的势利眼。在我和我那帮“学习好”的朋友们看来,能在高三从外地转到我们这样的学校,穿得又这么寒酸,家境应该不会很好,不会交得起高昂的转学费。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忐忑,希望能从他身上学到些新的知识点,也害怕他会在成绩上超过我们。他沉默寡言,上课总是很安静地看着黑板,说话时有些结巴,种种迹象都像是学霸的样子。
怀着一颗势利的心,我想尝试去接触他,和他交朋友。一天下午,我去水房,看见他拎着两个班里的公共暖壶打水。虽然我也很怕和陌生人交谈,但是势利心冲破了社交障碍,我和他说:“我帮你拎一壶吧。”
在回班的路上,我们聊了一会儿天,他虽然有些磕巴,但是很认真地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进到班里放下暖壶时,他对我笑了笑,说“谢谢。”
从那之后,他时不时会拿着作业本向我问问题,我努力回答,但也觉察出一些不对劲,因为有些问题并不难解,但他却解不出来。累积的怀疑,终于在第一次月考时揭示了答案。那次下分前,我的一位朋友抑制不住兴奋地对我说:“那个转校的一来,班里的倒数第一马上变成倒数第二了。”
必须承认,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长长出了一口气。那之后,我也听到了一些传闻,说他家里其实很有钱,他转学进来是花了高价。只是父母做生意,不管他,他自己也不爱打理形容,于是看起来“抠抠索索”的样子。
他学习很不好,长相虽然一开始受到一些女生的关注,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他的磕巴与沉默而归于零。他就总是这样坐着,听别人聊天却搭不上话。找我来问问题时,我依然会给他仔细解答,但是却多了几分不耐烦。——那时的高三流行一种迷信,认为和学习不好的同学在一起,会沾染到他的“衰气”,考试会考不好——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他常来找我,就开玩笑地和我说:“你和他这么近,别传染了他的衰气吧!”
因此,越是临近考试,我越是会有意减少和他的接触。而我渐渐发现,那些原先欺负我的人,都不怎么再搭理我了。毕竟,相比于一个中午顿顿吃牛肉拉面,还不知怎样就会“发神经病”的家伙,一个有钱、没背景、学习不好又沉默寡言的转校生欺负起来有意思多了。
我不知道他遭受过什么——也并不关心,只是有时下午上课前,他进班时校服总会比先前变得更脏。在同学无视的喧嚷中,他耷拉着头走到座位上坐好。如果他看到我在看他时,会给我露出一个微笑。
那天,我忘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大概是想找个清静地方背题,因此走到了教学楼后面的一个少有人走的楼梯间那里。

微电影《沉默难鸣》。
当我从走廊那头转过来时,我看见楼梯间前躺着一个人。是他。他横躺在那里,像个扔在地上的破布偶,胳膊和腿都软绵绵地张开着,因为校服和球鞋本来就很脏,所以看不出他遭受了怎样的欺凌。
而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左顾右盼看了看,确定那些人已经走光了,才敢走上前去。
我看见他的眼镜被扔在一旁,浓黑的眉毛下,那双总是含着阴郁微笑的细长眼睛睁得很大,无神地直直望着天花板。
我有些害怕,但还是叫了他的名字,他仿佛没有听见,眼睛也没有动一下儿。这让我更紧张了。直到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他,想伸手摸摸他的脖颈的脉搏,他才把眼睛转向我,很努力地笑了一下儿,低声呢喃说:
“对不起,对不起……”
他自己戴上了眼镜,攀着我的胳膊起来,直到此时我才发现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但因为快要模拟考试了,所以我很有些犹豫要不要扶着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出我那一刹那为难的神色,但是他却摆了摆手,只是扶着我的肩膀很努力地正常走路。
快到教室前,他忽然把手从我的肩膀放下了,自己一拐一拐地向前走了两步,回头笑着对我说:
“你真好,不讨厌我。”
一周多后,他又转走了,我没有再见过他。
沉默难鸣
我已经忘了,或者说,我也不想再重复一遍最终把我逼到楼道死角的那根稻草。也许我所经历的每一次欺凌,或许都可能把我逼到死角,只是,这一次,我扛不住了而已。就在那天上午,有同学觉得我眼神不对,但他开着玩笑对我说:
“你这眼神很狞啊,你不会变成马加爵把我们都锤了吧!”
而我只是微笑着低声说:“没有,没有……”在那一刻,我似乎有些明白了那名转校生微笑的含义。只是,我当时没有语言能表达,今天依然如此。
我坐在楼梯下的角落里,等着手腕的血流逝,但它流得如此缓慢,我有些着急,又恨恨地划了两刀,有一刀还划在了手背上,但血还是不疾不徐地流着。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去操场看看。于是我滴答着血,就像平时散步一样,走到操场上。
我躺在草丛间,仰望着星空。那璀璨的繁星之间是无穷无尽的黑暗,而所谓的光亮,就像是黑纸上用针尖戳开的几个小孔而已。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死,就如同繁星间的黑暗一样,毫无意义。
我的死不会让那些欺凌我的人付出代价,受到惩罚,甚至连让他们良知受到些许谴责都做不到,甚至,还会成为继续鼓舞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欺凌弱小的证据:看啊,我们把他逼死了,一点惩罚也没有。学校为了顾全大局,也会将我的死说成是我个人的心理问题,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即使是有同情我的人,也很容易被扣上恶意炒作,吃人血馒头的罪名,在汹涌的网暴狂潮中缄默无声。
我的同学会很快遗忘我,我的朋友即使愿意纪念,三个月、半年,就是纪念的界限。只有我的父母会为我悲伤终老。
活着沉默,死了同样沉默,有多少像我一样沉默的人,永远无法讲述自己被迫沉默的故事呢?
我不知道。
我已经习惯了沉默,当年校园遭受的欺凌,我选择了沉默。硕士老师剽窃我的论文成果发表,但最后我还是被劝着沉默——因为没有人愿意聆听,人们说:“算了吧……”
当我的朋友生前遭受网暴,死后遭受毁谤,想要为他讨回公正,但,周围徜徉的还是那句话“算了吧……”
于是,只剩下沉默。
但我也留下了一点点痕迹。在我编剧的动画《中国唱诗班》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有两部动画的主人公,都是被同龄人欺负的孩子。在最后那部《咏梅》里,被欺负踢打的小男孩周颢,与他保护的梅树化作的精灵,结下了一段情缘。许多观众觉得这个聊斋式人妖相恋的故事太老套。但,故事里的周颢,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