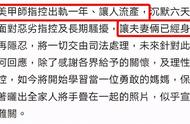梁晓声和父亲合影
大哥二哥兄弟情深 同度人生坎坷路我一直认为,大哥与二哥之间的兄弟之情,与大哥对二哥的影响及情感交流在跨跃人生不同年龄段对情感的不同认识,不同追求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我们家五个兄妹中,只有大哥与二哥之间的情感交流经历了童年和幼年阶段。
大哥与二哥经历了那次可怕的体罚后,秉性突变。大哥变得更加忧虑,沉默呆板。但学习却更加刻苦,似乎是一种超越正常人的刻苦。二哥也变得经常双眉紧锁,目光深沉,少言寡语,很少看到他那往日的甜甜微笑。
二哥和大哥的最大变化是相互间更加关心。正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才使得我们把极度贫困、饥饿的日子勉强维持下去。
那时大哥正面临高考,却经常饿着肚子上学。在饥饿和困乏中复习到深夜。看到大哥消瘦苍白的脸,二哥的眼圈湿润了。
一天夜里,二哥突然从梦中惊醒,见大哥还在刻苦复习,就想恳求大哥休息。可二哥连说了几声大字,也没说出哥字,脸却憋得通红。大哥惊呆了。我们也惊醒了……这是二哥自那次体罚后的第一次口吃。那以后,我们常听大哥对二哥说:“绍生,口吃是可以矫正过来的,不说话少说话都不行。不着急,一字一板地慢慢说,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如今二哥说话慢条斯理地就是那时按着大哥的要求逐渐养成的……
后来二哥常跟我们说起那天夜里他突然惊醒的事儿。他告诉我们,那天他做了一个恶梦,梦见他跟着大哥去买粮食,走到半路,大哥突然脸如纸龟,额头冒汗,身子一软倒下去……
我们听了,心里顿时紧张得很,甚至害怕起来…
半晌,二哥接着说:“大哥把粮食都省下来给我们吃了,自己饿着肚子上学,还要复习功课到深夜,我真担心我们的大哥有一天真的倒下去……”说着二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泣不成声了……我们兄妹三个也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那以后,每到吃饭的时候,二哥总是先给大哥盛出一碗,我们也从此不再抢饭吃了。
一九六二年春的一天,外面刮着七、八级的大风,我们兄妹三人正趴在炕头的箱子上写字、做作业。只听一声巨响,房梁断了,正砸在我与三哥之间空当的箱子上。原来房顶的烟囱被风刮倒了。
母亲回来后去找房东,房东动迁了。大哥从母亲满脸的愁面知道了结果,就对母亲说:“妈,你上你的班,不然会扣钱的。”然后转身对二哥说:“绍生,明天我找几个好同学,你也找几个好同学做帮手,找个车子拉点黄土把烟囱砌起来,把房梁顶起来,行不行。
二哥非常佩服大哥的果断,点头答应着。
第二天,大哥和二哥叫的同学都来了,有十几个。再加上邻居的叔叔、大爷、哥哥们,大家一起动手,上房的上房,拉土的拉土,不到一天的工夫,就把房子修好了。
可是,在顶房梁的时候差点出了一件大事:老房梁的柱子突然倾斜倒下。要不是二哥推了大哥一把,新顶起的房梁就会砸着大哥。
转眼秋天到了,安平街大杂院的邻居们大都动迁走了。我们住的歪歪房的门前挖了几条横七竖八的深坑,门也几乎让挖出的堆成山一样的残土拦住了。
一天夜里,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雨水顺着几米高的残土坡上冲泻而来。片刻间,我们的家一片汪洋……母亲和大哥二哥去找动迁办的人,可半夜三更上哪去找呢!母亲只好敲开邻居家的门,全家人在那熬到天亮……那天直到母亲领着我,抱着妹妹找到当时的市人委信访办,动迁办才派来几个人用一台抽水机把屋子里的水抽干……
那一年的第一场大雪过后,我们全家坐在一辆马车上,连同那些破烂的家当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安平街43号大杂院,来到了光仁街大杂院,重新开始了我们家的平民生活……
一九六四年,大哥终于如愿以偿,接到了唐山铁道学院的录取通知。这真是我们梁氏家族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啊!
可父亲却来了一封信,告诉大哥不论考没考上大学,都不能念。家里弟弟妹妹多,父亲一个人挣钱,难以维持,还是找个工作吧!
当我们全家从一时的兴奋中回到现实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我们的家境根本无法供大哥上大学。
后来大哥只好放弃了大学的念头,请邻居张叔帮助找一家小铺去卖菜……那段日子是大哥二哥内心世界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此时的大哥突然感到人生的暗淡。二哥为了尽力照顾大哥,抚平大哥心灵的创伤,就经常去给大哥送饭,借机劝劝大哥一定要挺住,放宽心……
一天,哈一中的白老师突然到我们家问梁绍先怎么不去报到?母亲一一告诉了他。白老师说,有困难,唐山方面可以给助学金……
母亲和大哥听了,如同遇到了救星,连声答谢。后来大哥看了看白老师和母亲说:“妈,咱家穷,供不起我上大学,学院能给我助学金,我再挣点稿费,不要家里一分钱,让我去上大学吧母亲点了点头…
大哥走那天,母亲和我们兄妹都哭了。是二哥一直把大哥送上车站的。二哥当着我们的面只是掉了几滴眼泪。可是当列车就要开动时二哥竟痛哭起来。
大哥说:“绍生,别哭了。我去上大学,既是大哥今生今世的梦,也是母亲辛劳拼搏的梦。我去上大学,梦就圆了。可你的担子就重了。你千万要照顾好母亲和弟弟妹妹呀!”
大哥就这样上大学了。二哥为了挣点钱帮助大哥度过难关,曾拉过小套,扒过树皮,掏过大粪。可是二哥没能挣到几个钱……直到今天,二哥常为此感到愧对大哥……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收到大哥学校的一封电报:梁绍先病重送归哈。

不久,大哥被送回哈尔滨。住进了哈尔滨精神病院。几个月后,大哥病情好转出院了。母亲、二哥和我们全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大哥好了一点就急着回唐山上学。二哥对大哥说:“不要急着回去,再多恢复一段日子。”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二哥正在家修理房子抹墙,大哥乐呵呵地从外面进屋对二哥说:“绍生啊!*号召上山下乡,户口我已经给你迁好了,你还是下乡去吧!”
二哥也乐了,以为大哥真的好了,就深沉地对大哥讲:“我早就打算下乡了,就是对你的病不放心,现在你好了,你可千万要照顾好这个家呀!”
二哥说到这突然想起他送大哥上大学,大哥在站台上对他说的话……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二哥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贫穷,大哥也许不会患病;如果不是因为贫穷,我也许不会成为作家。”
二哥毅然奔赴边疆 兄弟情意埋在心中二哥下乡在黑河兵团一师,与原苏联只隔一条江,是反修前哨。那里气候寒冷,条件艰苦,但每月可以拿到40余元钱的工资。二哥不吸烟,不喝酒,有时间就看大哥送给他的书。平时他省吃俭用,把钱积攒起来。他惦记家,几乎月月给家来信,每封信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哥的病情好些了吗?
一九六九年,二哥让他的兵团战友给家里捎来一旅行袋中草药,足有几十包。那位捎药的大哥说,这药是用北大荒一位老中医祖传的方子抓的,听说用这个方子曾治好过几个精神病患者。这些药是一个疗程。为抓这药二哥把所有的积蓄都用上了,又向几个战友借钱才勉强凑够……有几味药不好抓,是求熟人在药材公司批出来的……
后来大哥服用了这付药,病情还真见好。他看到母亲成天在毡毛飞扬阴暗潮湿的五七厂絮鞋帮儿,心里非常难过,就想找个工作干,不让母亲受这份苦了……二哥得知后,一夜也没合眼。他给大哥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王铬起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大哥的病好了,求她给找个代课的工作。正好王老师的爱人韩老师那的五十七中缺一名语文老师。这样大哥就开始了教师工作的生涯。那时大哥语文基础是拔尖的,所以学生反映特别好。那是一九七O年的事。
大哥好了,当老师了,街坊邻居有祝贺的,有羡慕的。委组长开始向母亲提亲了,说是她的亲外甥女,叫徐淑杰。
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就千里迢迢赶回来,花尽了十几年的积攒为大哥成了家。二哥知道后高兴地给大哥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哥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生气,要保证不胡思乱想,更不要工作太劳累。二哥因农忙没能请假参加大哥的婚礼,就东借西借凑了二百元钱寄回家中……谁知这门亲事竟埋下了大哥终生痛苦的种子……
一九七一年的一天,大哥和大嫂结婚数月,突然因为父亲给大嫂买的那块手表发生了争吵。大哥说上课需掌握时间,先把表借给他带吧?大嫂当时就火了,没给大哥,并乘大哥不备用斧头把表砸碎了。大哥发现后,掀翻了桌子,要打大嫂,被母亲和我连说带劝拉住了。可大嫂却打点包裹,谎说上她大姨家住一宿。第二天一早竟回了双城娘家。那时大哥当代课老师已经快到一年了,学校正要研究给大哥申请转正。可大哥不久就犯病了……
大哥犯病后,开始自言自语,满街走。那时三哥也下乡了,妹妹还小在上学,我刚刚上班。只有母亲一天提心吊胆地跟着大哥,生怕大哥在外惹事……
一九七二年,因为与学院联系不上,没钱让大哥重新住院治疗,大哥的病开始越犯越重。一天,大哥突然发疯,把他结婚买的镜子、闹钟、花瓶等都从窗子扔到外面,还把被单褥单撕成条条……再后来,大哥几乎把家里东西砸光、毁尽,而且开始打人。没有办法,只有找派出所派人把大哥捆绑起来,关在一间小屋里……
大哥被关在小屋不久,二哥突然回到家中;原来二哥在北大荒写儿童文学出了成绩,省出版社调他回来整理他的几篇儿童作品,准备出版。
二哥看到这个几乎破碎的家,和大哥捆绑在散发着霉味儿的小屋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与大哥抱头痛哭起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家竟如此悲惨……半晌,二哥止住了泪水,望着被折磨得憔悴万分的母亲说:“妈,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大哥送医院去吧!……”
在母亲和二哥,居民委的帮助下,市民政局终于批准大哥半费住进了精神病疗养院……从那以后,大哥的住院费问题,又成了二哥的一大负担。
一九七四年,二哥被兵团推荐到上海大学学习,他也开始体验大哥上大学时的窘迫。多亏他几个同学,几个要好的兵团战友帮助他。可是他还是得了黄胆性肝炎。如果不是二哥的坚韧,他的大学也几乎半途而废。
一九七七年,二哥终于度过难关,完成学业,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时一无所有的他,开始从每月几十元的工资里,抽出20元钱,为大哥交住院费。
他来信告诉我,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再也不要把大哥捆绑在小黑屋里……
大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那所医院。
二哥开始实施拯救大哥灵魂的工程一九九九年“五一”前夕,二哥突然神秘地来到哈尔滨,到医院把大哥接到哈尔滨华侨宾馆。他告诉在华侨饭店工作的老同学刘树起,我回哈任何人也不要告诉。我专为大哥而来。我要与大哥在你这住几日,然后作出一个对得起大哥,又使我心里平静,让母亲在九泉之下安心的决策。
二哥一见到大哥,心里顿时一阵酸楚。如今的大哥,佝偻着干瘪的身子,灰暗呆滞的目光,嘻嘻傻笑的痴态,脏兮兮的邋遢样子,令他怎么也找不剖童年时代大哥的影子了。
二哥对大哥说:“大哥,今天我把你接走,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你愿意吗!”
大哥起初有些受惊。听了二哥这样问,顿时张开嘴嘿嘿地笑起来,边笑边说:“愿意!愿意!那还不愿意!”就这样二哥带着大哥离开了疯人院。
二哥把大哥接到宾馆的第一件事,便是先让大哥洗澡,还亲自为大哥搓澡……
大哥似乎不好意思,坚持自己搓。他的意识似乎还停留在60年代他生病之前。来到这豪华宾馆对他来讲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洗完澡,二哥让大哥自己换上新衣服。衣服是二哥亲自买的,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是新的。
他说,这样做是让大哥有一种新生活开始了的感觉。他让大哥自己穿,是看看大哥的自理能力。
接下来便是餐饮。为了让大哥逐渐与现代都市生活相适应,特意定了一个星期的单间。并每日三餐把菜谱递给大哥,告诉大哥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听大哥说点这些菜要花很多钱的。二哥的心又是一阵酸楚。竟使二哥联想到大哥上大学,饥饿难熬,穷困潦倒的窘迫情景……
二哥对大哥说:“我就是让你点你想吃,但从未吃过的莱,就是让你把钱花了,享受了,我才开心……”
但大哥还是不解,只是说:“绍生,还是你点吧!我只要一盘刀鱼,再吃什么都行……”

梁晓声与大哥
几天来,二哥总是同大哥在一张床上共同休息,梦想大哥会重现童年的美好回忆,尽快与大哥感情沟通,温暖三十年来大哥那颗已经变得冰冷的心……
一个星期过去了,二哥决定带大哥回北京。那天去了很多人,有大哥的同学,二哥的同学及哈市我们兄妹三人……
二哥对我们说:通过一周的时间我与大哥朝夕相处,我认为大哥换个环境一定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我带走大哥是有理由的。大哥能自理;不能犯病伤害我及其他人;我为大哥准备的房子、家具、电器等都是崭新的,有利于大哥身心健康;我还雇了我们老邻居二小照顾大哥……
在场的人对二哥的决策都没有疑义,担心的是怕给二哥、二嫂增加负担,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特别是影响二哥的写作。
其实,我理解二哥的苦心,他总梦想大哥有一天真的好了。因为二哥曾对我说过,如果大哥真的好了,他就在北京给大哥成个家,让大哥晚年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的心里也是矛盾的。我知道大哥住在医院里是委屈的,但作为病人也是无奈的。二哥能接大哥去北京,对大哥来讲是到了天堂,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我见大哥的次数会少了……我有很多观点,在二哥面前只有沉默,因为我不能用我的观点刺伤二哥拯救大哥的一片苦心……就在那天晚上,二哥带着大哥、二小去北京了……
2000年,我专程去北京与大哥住了段日子。真是令我感慨万分,一种对二哥二嫂发自肺腑的敬意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
多么令人敬佩,—个社会活动频繁,一年要写几十万字的作家,二哥梁晓声;一个起早贪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又能精心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孩子的二嫂焦丹;竟能无怨无悔,竭尽全力地让一个疯大哥体验到生活的美好,亲情的温暖,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气……使大哥那颗冰冷的心开始融化……
大哥住的地方是二哥在北京西三旗金达园小区,花三十余万元购买的一套居住面积一百多平方米,四室一厅的豪华型住宅。
室内布置着全新的高档豪华家具,家用电器,及造型各异的工艺品;崭新的书柜里面摆放着几十套世界名著及二哥的部分著作……那是专供大哥欣赏的。
客厅中间放着一台雅玛哈电子琴,是为大哥闲闷时弹拨的。
靠阳台一间十几米的居室,是大哥用来练书法的地方。一张方桌,靠背椅放在那里。桌上摆放着二哥朋友送的西瓜大小的防制古砚和大小不一的狼毫毛笔,旁边放着厚厚的一叠白纸。二哥说,这是让大哥修身养性的最好办法。
二哥对我说,他给大哥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六点半之前起床,自己叠好被褥,打扫好房间,洗漱后到阳台锻炼身体,抻抻筋骨。
饮食方面,一日三餐,鱼肉菜搭配合理,一周可按大哥要求去饭店吃一次家里不能做、大哥喜欢吃的饭莱。
二哥还针对大哥不爱看书、练书法、弹琴、只想吸烟的恶习采取了硬性措施。每天练琴一小时。练习书法达百字。朗读小说五千字。还嘱咐二小要把大哥的烟控制在十支以内。
二哥还为自己规定,今后除重大外事活动,谢绝一切采访。每周内看大哥的次数不少于两次。二哥二嫂还定期接大哥出去逛街、游览、上饭店、接回家吃团圆饭……
他说,这些做法对早日克服大哥在医院养成的陋习,过正常人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说这些话时,二哥俨然一个上帝派来拯救大哥灵魂的使者。
但我清楚,大哥还是病人,实施起来肯定有困难,不能急于求成。但对二哥怀着一片同胞兄弟真情,企盼大哥出现奇迹的心情,又怎忍心泼冷水呢!
我在北京住的日子里,有几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梁晓声与妻子、孩子
二嫂几年前就要买车,二哥始终不同意。可为了看大哥方便,二哥主动让二嫂买了一台富康车。
一次二嫂在单位开运动会把胳膊摔骨折了,包着沙布,打着夹板,还坚持开车去西三旗看大哥……多好的二嫂啊!
一次,两位外国记者事先没有约定,要采访二哥。可二哥答应了大哥一同出去游玩。二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推迟一天接受采访。两个外国记者得知内情后,不但理解了二哥,而且更加敬重二哥。他们说:您的做法真令我们感动,我们将针对您对您的病哥哥的感人故事进行一次专访……
与大哥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我慢慢发现,大哥的脾气基本没了。柔柔的,很听话,二哥的大部分要求他都能努力做到。就是对控制他吸烟,有时不高兴。其实这点我理解大哥。好人都难以戒烟,何况一个吸了好多年烟,嗜烟如命的精神病患者呢!
二哥每次来看大哥,先是看被子叠得整不整齐,摸这摸那看看有没有灰尘,翻开大哥的衣领看看是否脏了该洗了……再就是对大哥说得最多,的那句话:大哥,这里就是你的家。二小既是为你服务的,又是按着我的要求帮助你逐渐养成好习惯成为正常人的监督者。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尽快成为正常人。
二哥也吸烟,但每每看到大哥烟不离手,把烟灰掉在地上,就直皱眉头,有些生气。并关心地对大哥说,你在医院得过肺病,还拼命吸烟,对你的身体能有好处吗?
有一件事,想起来至今还令我感到内疚。
那天大哥的烟已经吸了十支,可烟瘾又来了。我渐渐认识到烟对大哥来讲简直就是大哥的精神支柱,想改变比改变他的精神还难。大哥吸不到烟,就在屋子里急的团团转,后来又说出去走走,我答应了,但还是不放心地偷偷跟在后面。果然,见大哥竟满地捡起烟头来,并向一个吸烟的人借火对着了,深深地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
二哥来了。我把大哥捡烟头的事全归罪于二哥的苛刻,与二哥大吵大闹了一场……父母在世时,认为二哥说的话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却成了我们家第一个敢与二哥争吵的人……
我走那天,二哥又推辞了一位法国记者的采访,送给我几本他写的新书。又陪我在西三旗散步一个多小时。他边走边对我说:“绍文,还生二哥的气吗?其实你根本不理解二哥心中的苦涩。妈妈爸爸都走了,我们兄妹最亲近的人就是大哥了。我是多么希望用我现在做的一切,使大哥真的好起来呀广说到这二哥流泪了……他接着说:“我不但为大哥买了房子,我还求朋友联系了一个安徽女人。她的丈夫出了车祸死了,她一个人带个孩子,生活艰难,很愿意与大哥成个家。可大哥如今的状况,我怎么能够答应人家呢!那不是坑人家嘛!”
听到这,我也哭了……
二哥一直把我送到车站。临上车时,二哥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车开了再看吧!……当我打开信封时,里面装了二千元钱……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几个月后,二哥打来电话告诉我:二小得了肺结核,他给了他很多钱,让他回哈尔滨住院治病了……
他那时找不到满意的保姆照顾大哥,把大哥送到了一家条件较好的疗养院。尽管费用高,但大哥会生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