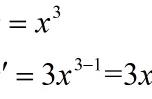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神学、政治、赞美诗方面的拉美弥赛亚
1925.1.20 - 2020.3.1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1925年生于格拉纳尔,先后就读于墨西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54年,卡德纳尔参与了四月革命,政变流产。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成立后,卡德纳尔成为桑解阵的核心成员,桑解阵在1979年一举推翻索摩查政权,卡德纳尔旋即被任命为独立后的尼加拉瓜文化部长。早在1970年,卡德纳尔就为马克思主义所折服。1987年,卡德纳尔又辞去文化部长一职,表达了对政权的失望,他所支持的“桑地诺革新运动”(Movimiento de Renovación Sandinista)始终只是少数党。在最近的十多年,卡德纳尔和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权越来越不和,卡德纳尔再次成为一个直言者。
卡德纳尔最为人所知的形象是,他跪在停机坪,脱下黑色贝雷帽,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致以亲吻。卡德纳尔在1956年皈依了基督教,在托马斯·默顿的指导下,卡德纳尔在圣母特拉普修道院修行。回到尼加拉瓜后,他继续传播自己的宗教,并于1966年在索伦蒂纳姆群岛(Solentiname Islands)建立了一个艺术殖民区,以绘画和挂毯闻名于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反对解放神学组织的神学阐释,而卡德纳尔正是它最重要的代表。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卡德纳尔坚信基督和马克思可以并行不悖,对卡德纳尔来说,福音书是共产主义的,天国可以由社会主义者们建立在一个更平等友爱的大地之上。但卡德纳尔遭受到的是他的教士权于1984年被撤销。
卡德纳尔的诗歌表达了现实,同时吸纳了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神秘等诸多方面,这是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表达的。卡德纳尔大部分的诗歌是私人的,回忆青春、渴望爱情、记录履历等等。和同时代的诗歌不同之处在于,卡德纳尔试图从进化论中获取启示。“在一个充满冲突、焦虑、战争、残忍和困惑的时代,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卡德纳尔的所写是一首赞美爱的赞美诗,”托马斯·默顿如是评价卡德纳尔。

杨牧:渐进至现代的古典文学大师
1940.9.6 - 2020.3.13
杨牧,本名王靖献,于1940年生于中国台湾花莲,爱荷华大学创作硕士,柏克莱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博论为《钟与鼓》(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杨牧曾任华盛顿大学教授,后回到台湾地区,在台港两地办学任教,晚年他主要在东华大学教学生活。此外,杨牧还参与主编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参与创办洪范书店出版社。
在中国现代诗即新诗的历史中,大多作品保持着和古典的距离,特意做出一个“新”、一个“现代”。只有少数的诗人在古典的世界采撷、挪用,杨牧是其中做的最好的一个。奚密视其为“Game-Changer”正在于此,他就像他所崇尚的浪漫主义者们一样,秉持着对古典的信奉,为当时代开了一种新风。
像西学中的德莱顿、阿诺德、艾略特,也像中国传统的大多数文人或者陆志韦、卞之琳、吴兴华、叶维廉等人一样,杨牧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执迷的、独特的看法。据他说,中国文学确实有自己的史诗传统,不过它并非如西学中的那么完整和尚武。中国实在是有自己的The Weniad(对照Iliad),它分散在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和早期民谣中,这些诗歌都有着对于社稷、国土、人民和文化的殷切表达,它们从尚武精神中割裂开了,形成了一种委婉、富丽、忧患的精神。
按照旧的阐释去对待“发乎情”、“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是一条末路,我们需要用现代语言和现代观念去再现中国古典诗歌所蕴含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海外学者所指出的抒情传统虽然可贵,但存在偏颇,例如它实则聚焦于现当代中国文学而非古典文学,聚焦于细情而非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抒情一则神秘化和彰显了主体,所用形式是儒家的而非基督教传统或其后继浪漫主义传统的,再则它在神秘经验、泛神论思维和世俗经验、日常思维之间做出并置和融合,三则它无所不在的为“他人”而作,将叙述和意义引向一个虚无而博大的关怀之中。 杨牧认识到了古典的价值并谦卑地实践,他在《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一文中写道,“潜心古典以发现艺术的超越,未始不是诗人创作的必要条件”。
诗人最广为流传的一句或许是“凭藉着爱的力量,一个普通的/观念,一种实践。爱是我们的向导”。这或许是对美丽岛事件和政治的窘迫的回应,或许是对过往历史的喟叹和升华,或许是对自然万象的流转和迁变的惊骇和醒察。然而,它毫无疑问展示了诗人向古典、宁静、中国诗、诗的永恒的迈进。诗人的一生便是如此迈进的坚持、探索、试验和辛劳。他便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但年代湮元,乐府毁坏之后,何尝有(诗人)这种职业呢?”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Ю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ондарев):苏联战壕真实派代表
1924.3.15 - 2020.3.29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于1924年生于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后迁居莫斯科,于1942年入伍,投身伟大卫国战争,先后参与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解放基辅、攻入波兰和捷克等战役,最后生还。战后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学习,师从大作家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整整三年,他教导我们文学创作最主要的就是说自己的话。”一生中,邦达列夫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文学奖、国家文学奖等国家奖章,还曾任作家协会主席。
邦达列夫是苏联文学战壕真实派、全景文学的代表。解冻时期,邦达列夫敏锐地判断出形势变化,自觉地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路线服务,发表《营请求火力支援》(Батальоны просят огня),一举成名,打开了苏联战争文学的新天地。其最为知名的作品是《热的雪》(Горячий снег)、《岸》(Берег)、《选择》(Выбор)、《演戏》(Игра)。邦达列夫的作品往往人物众多,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情节发生的地点,忽而前方、忽而后方,多层次多线索地开展,具有交响乐和史诗的效果
“有限的活动地点、短暂的故事时间、为数不多的人物以及围绕中心人物展开事件,这是战壕真实派小说的共同特点之一。”陈敬咏在《邦达列夫创作论》一书中指出,“因此有的评论家把它称为新三一律。”
他在《瞬间》中回忆道,“我们这一代人从战争中学会了爱和信任,学会了恨和否定,学会了笑和哭。我们学会了珍惜那些在和平生活中由于司空见惯而失去价值的东西,那些变得平淡无奇的东西。〔……〕在街上偶尔看到的女人的微笑,五月的黄昏那蒙蒙的细雨,水洼里闪现着的路灯的倒影,孩子的欢笑,第一次说出的’妻子’这句话,以及独自做出的决定。”

鲁本·丰塞卡(Rubem Fonseca):二十世纪巴西最伟大的作家
1925.5.11 - 2020.4.15
鲁本·丰塞卡,于1925年生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茹伊斯迪福拉(Juiz de Fora),葡萄牙移民后裔,曾就读于前巴西大学法学院,于1952年成为一名警官,主要在警察局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丰塞卡于1958年离开警察部门,后来担任巴西社会研究所(Brazil’s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and Research)所长,该所支持1964年的军事政变及随后的政权。一生中,丰塞卡追随托马斯·品钦,拒绝媒体保护个人隐私。2003年,丰塞卡被授予卡蒙斯奖(Camoes prize)。2015,被授予巴西文学院的马查多·德·阿西斯奖(Brazilian Academy of Letters’ Machado de Assis prize)时,他发表感言说,“我是一个特殊的人,特殊到并不足以解释自身。”
丰塞卡的作品包罗万象,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等等,其中最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主要作品有《新年快乐》(Feliz Ano Novo)、《大艺术》(a Grande Art)、《 蟾蜍和斯帕兰扎尼》(Bufo & Spallanzani)、《阿戈斯托》(Agosto),等。诚如巴西诗人、批评家卡洛斯·内加尔(Carlos Nejar)的观察,丰塞卡的热情(pathos)更多倾注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因为这是一个简洁、直接的灵魂,在长篇小说的拖沓中难免生厌……短篇小说是智慧的极限。”
《新年快乐》诞生于1968年《第五制度法案》之后,民主化之前的一个阶段,怀有民主诉求或左派思想的文武官员、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在独裁的高压下溃不成军,或隐忍沉默,或拿起武器成为游击战士。甫一出版,《新年快乐》就遭到了封禁,阿弗兰尼奥·科蒂尼奥(Afrânio Coutinho)为其鸣不平,写下《文学中的色情》,“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首要原则是看它的艺术成就。〔……〕莎士比亚写下whore与鲁本·丰塞卡打出puta这个字眼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丰塞卡的作品中,他往往借警察或私家侦探的视角,描述残忍、激情、污秽、犯罪等。在学者樊星看来丰塞卡的文学特色之一在于他在巴西都市文学中开启一种“硬对抗”的写作模式。“之前巴西文学比较多的是 ‘软对抗’,以嬉笑狂欢、满不在乎为主,代表人物是亚马多笔下的流氓形象,而丰塞卡笔下的角色是真正的暴徒。另外,可以说里约这座城市在他作品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他作品中 ‘对立’ ‘分裂’感的主要来源。”正如译者符辰希所说,鲁本·丰塞卡为我们讲述的骇人故事,并非个别心智不全、仇视社会之徒的极端案例,而是强权统治下巴西社会必然要遭遇的悲剧,一个同时属于穷苦人与特权派、施暴者与受害者的悲剧。
深居简出的丰塞卡在一次罕见的演讲中说,“我写了30本书,里面全是下流的话……我们作家不能歧视文字。一个作家说我不能这么说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是在写儿童读物。每个词都必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