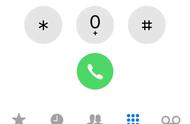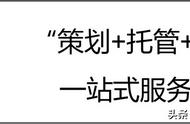不曾到过异邦却心存向往
不曾到过异邦却心存向往,
而对熟悉的故土却诸多责难,
我总在说:在我的祖国,
哪里有真正的智慧,哪里有天才?
哪里有灵魂高贵的公民,
为炽热的自由而大声疾呼?
哪里有这样的女人――热情、迷人,
又生动活泼,她的美丽并不冷酷?
哪里能找到无拘无束的交谈,
快乐、自由,而又才气横溢?
我和谁无须作冰冷而空洞的应酬?
祖国啊,几乎让我感到了仇恨――
可是,昨天,我见到了高利金娜,
从此,我不再对祖国有任何怨言。

复活
野蛮的画匠以稀松的笔法
把天才的一幅作品抹黑,
毫无意义地在上面描画
自己不成章法的劣作。
许多年过去,互不相容的颜色
像枯朽的鳞片一般脱落;
在我们面前,天才的创造
再度呈现往昔的美丽。
伴随着我痛苦的心灵,
我的困惑就这样消失,
在这幅作品中,仿佛幻景似地
复现了最初纯洁的时日。

我再也不会有什么期待
我再也不会有什么期待,
我再也不会爱什么幻想;
惟有痛苦还伴随着我,
那是心灵空虚的果实。
在残酷命运的风暴下,
我鲜艳的花冠已经枯萎;
我孤独而忧伤地生活,
我等待:末日是否已来临?
就这样,忍受着暮秋的寒意,
仿佛听到冬天风暴的呼啸,
如同一片弥留的树叶,独自
在光秃秃的树枝上颤栗。

神奇的往昔时光的女伴[1]
神奇的往昔时光的女伴,
我忧伤而戏谑的虚构之朋友,
我在生命的春天与你相识,
那时充满最初的梦想与欢娱。
我等待你;在黄昏的寂静中,
你来了,像一名快乐的老婆婆,
穿着棉背心,戴着大眼镜,
手摇铃铛坐在我的身旁。
你一边晃动着儿童的摇篮,
一边用歌声让我的耳朵入迷,
你在我的襁褓中留下一支芦笛,
这支芦笛被你施了魔法。
童年逝去,像一场飘忽的春梦,
这无忧的少年曾蒙受你的宠爱,
在显赫的缪斯中他只记得你,
也只有你在悄悄地探访他;
莫非那不是你的形象,你的打扮?
你的形象改变得多么快速!
你的微笑像火焰般燃烧!
致意的目光仿佛火星在闪烁!
你的外套如同汹涌的波涛,
勉强遮盖着你轻盈的身躯;
你满头卷发,戴着一个花冠,
诱惑者的脑门散发着芬芳;
在黄色的珠链下,雪白的胸脯
微微泛红,轻轻地颤动……
[1]本诗献给普希金的乳母阿利娜·罗季奥洛夫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