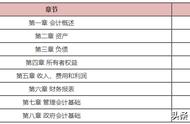随笔 / 小秦
合欢树象征着母爱与亲情,撑起一片荫凉,庇护孩子,播撒希望。生活很苦,很无奈,母亲种点花草,也是苦涩中的点滴生机。这棵树,却无意中撑起了另一个孩子的全部童年,个中机缘,谁又说得清?
从有我的“姑娘”到忘我的“母亲”,不顾自己的病,全部心思都在子女身上,母爱的伟大在于平常,在于从不放弃希望和自己的孩子。
母亲的愿望——孩子好好地活下去,哪怕还有一点点希望。对待孩子,就像对待这棵合欢树的成长,一等就是好几年。
关于生命的张力,还有季羡林的散文《清塘荷韵》,他播下莲子,第一年不会出芽,第二年也看不见,第三年才有微小的几个叶片,但是第四年、第五年就会发满整个池塘!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静待花开,尤其是对孩子的成长,时间会证明一切,急不得,更不能揠苗助长。
母亲为我,从寻医问药到借书看电影,因为有希望撑着生活。母亲的早逝,还是因为操劳和忧思过度。史铁生从生命角度写出的母爱比“临行密密缝”的母爱更为坚韧,从忧虑“生离”到畏惧“死别”,这是面对疾病和生命时的母爱。虽然人力是那么孱弱,但这种情感却是那么忘我,那么伟大。
史铁生剖析了自己的灵魂,残疾后,他只顾自己的痛苦,并不考虑母亲的感受和身体状况(《我与地坛》整个就是跟母亲“捉迷藏”,作者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没有考虑到母亲的双重煎熬,因为他还太年轻,不懂。“养儿才知父母恩“,由于史铁生自己没有子女,所以很难完全体会到母亲的感受,他主要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忏悔,去回忆母亲。
合欢树,其实是悲情树,但悲伤中有坚韧,有希望。
史铁生,我懂,他不想让自己就此“废了“,他要挣扎,渴望成功与掌声。
但老街坊们似乎并不在意他的文学成就,因为那不是她们圈子里的事情,并不重要(这里似乎是反讽:啥才叫“成功“呢?),大家还是问他的腿,回忆他的母亲,那棵树成了唯一的寄托和话题。
种树,是一种奇特的生命体验。当看见若干年前自己种的树,会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也会油然而生一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我曾经种过一颗无花果树,若干年后,又搬了三四回家,但那些老居民还记得当年有个教员种的无花果树,每年大家都采摘果实,品尝甘甜……直到那几栋楼被整个拆除,夷为平地。我和我的无花果树,便只存在记忆之中了。

所以,史铁生说:“我不在地坛,而是地坛在我。”
那个特别的时空节点,一去不复返,只是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
就像我的无花果树。
史铁生的生命题材作品可以打通阅读(包括散文《合欢树》《我与地坛》和小说《命若琴弦》),内核是对生命质量的渴望,是对人生希望的设定,基调悲凉,过程悲壮,但也要轰轰烈烈地奋斗一番。他因为独特的经历,感悟了生命,一路拼搏抗争,*出一条成功的文学之路,引导读者自己去感悟生命的意义。
我是谁?为什么我是我?这辈子,我要干点什么?


请读原著:
合欢树
史铁生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1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2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