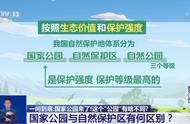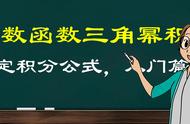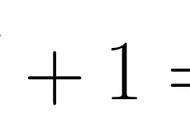《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书影。本书以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的万牲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与陶然亭为个案,借以一一对应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政治团体这五种人群的生活及表现,同时也分别反映公园所承担的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政治等功能,借此折射清末民初北京的现代性转型。供图:北京大学出版社
十年前,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我赴哈佛大学访学,着手北京公园的研究,起手写的就是“世界人的乡愁”,这部分最后成为本书的附录。在我当时的笔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第一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以“大地各国园林”皆为我所有、四海为家的气魄,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投射了个人意气风发的心态。十年后,我再赴哈佛访学,为即将出版的书稿撰写后记。当我翻看自身多年前所论述的康有为在“国人”与“世界人”的身份认同之间往返挣扎,尤其是康有为自剖心迹的“临睨九州,回头禹域,则又凄怆伤怀。故乡其可思矣,亦何必怀此都矣”等语,不由心有戚戚,感慨万千。十年一觉,大梦初醒,恰好为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画上一个圈。
我们这一代中国80后大多有儿时学校组织赴公园春游秋游的经历,列队去福州小西湖改建的“西湖公园”,归来还要统一写作文,是福州小学生每年的例行公事。而我自小长大的家毗邻福州的“温泉公园”,迄今假期归家,我依然会保持饭后与母亲赴公园散步的习惯,“红歌大家唱”和广场集体舞更是母亲每晚的保留节目。当时的我尚不明了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空间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但私人的感性经验,却使我对于公园始终怀有天然的敏感和亲切。现在想来,这两个公园其实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典型的公园模式:前者是将既有的中式传统园林开放,后者则是另起炉灶的西式绿地公园。同时,上述对于公园的两种使用方式——青少年的春秋游,与中老年的广场舞,实际上都与共和国时期对于公园作为“人民的公园”之蓝图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常遇到同行学者或关心或怀疑地问我:为什么要做公园研究呢?也许正是这些切身的经验,令我深刻地体认到,这种不为宏大叙事所关注、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空间与生活的实践,却在人们实际的生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我尝试做的,恰是打捞这些历史缝隙日常生活的碎片,复原历史的丰润和幽微之处,追问物质空间对于精神世界的意义。当最初的思考沉淀为博士论文选题的设想时,导师陈平原教授极力赞成并慷慨地一挥手,神采飞扬地说:我曾经打算退休以后,写一本书,叫作《来今雨轩的过客》,现在这个题目送给你了!其实,北京公园空间的背后,是城市研究、北京研究的视野,我对此的兴趣,就起源于陈老师的启蒙。陈老师是最早倡导北京研究的学者,当2004年我入读北大中文系本科时,陈老师与王德威老师主持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盛会刚于一年多前闭幕。有一堂现代文学史课上,陈老师给我们讲老舍,将北京会议的大幅海报带到课堂上给我们展示,背景是一帧著名的老北京照片,黄昏城墙下的骆驼队。陈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青年时初下火车对于北京的第一印象,那冬日清晨混合着豆浆油条和煤炉气味的凛冽气息,深深地触动了我。
公园题目有趣,但材料细碎,如何架构并以小见大,殊为不易。如今的章节结构,是经与北大中文系诸位师长陈平原、夏晓虹、王风、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姜涛等反复讨论而成形,选取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公园,以点带面,辐射不同的人群和功能。尤其是夏晓虹教授,她与陈老师是学界公认的神仙眷侣,二人指导学生的方式也是珠联璧合。我最开始试写了两版陶然亭的样章,陈老师都觉得公园的面目没有出来,在夏老师的建议下,我没有立即修改陶然亭,而是另起炉灶,新写万牲园一章,这也是夏老师主持的“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项目的一部分,近期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成文之后,夏老师评价挺好的,而陈老师没有再说什么,只张罗帮我投稿发表,我明白,这就意味着我终于找对方向了,可以这么做下去。接着又一鼓作气写了北海一章,同样是夏老师先帮我把关,陈老师只管拍板发表。就这样,在两位恩师配合默契的“保驾护航”之下,我的博士论文终于“上道”了。
我深知公园这个题目在文学领域颇显异类,但历次开题与答辩,先生们皆以博大的胸怀、开阔的眼界包容并鼓励我的创新,感谢钱理群、陆建德、孙郁、解志熙、李今等诸位学者。我很感激在我年少的时候,遇到的前辈学者都是如此光明纯粹的人,他们向我敞开了学术界最理想主义的一面。当我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书时,感谢董玥、宋伟杰、季剑青三位学者对于书稿的审阅和指正,他们对于北京研究都有代表性的著述,我自身的研究也受他们启发颇多。感谢王芳师妹为我悉心绘制藏书票,以及“河出图”智慧文博数据库提供的图片。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致谢几位学者,他们对我的公园研究有特殊的意义。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封面封底展开图。供图: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是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也是我城市研究的入门书,我因他来北大客座而结识,此后我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期间,两地互动,又有了更深的交往。因我能小酌一杯,又都是性情中人,李老师笑称我是他的“小酒友”。有时去香港看他们夫妇,我和李老师就先在其家附近的餐厅碰头,喝一杯李老师钟爱的scotch,畅聊学术,李师母再出门与我们会合,共进晚餐。因疫情等种种原因,我已三年不曾到香港,每每念及一老一小纵饮畅谈,至精彩处抚掌大笑的快乐。瓦格纳与叶凯蒂这对学术伉俪,他们都是整个生命与学术血脉相连、满怀赤子之心的学者,在城市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在我尚未确定题目之前,瓦格纳先生即已提示并鼓励我从事公园研究,从北京到波士顿,他们一见到我,总是热忱地询问我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向我推荐相关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我永远记得瓦格纳老师客座北大期间,我陪他与叶老师去食堂吃饭,在喧嚷的北大食堂里,瓦格纳先生穿着笔挺的毛呢西装、一丝不苟地打着领结,津津有味地谈论学术,与周围的环境形成某种反差。突然,一个小饭粒掉在了他的西装领子上,瓦格纳先生丝毫没有停顿,一边继续投入地谈着研究,一边自如地捻起饭粒放入口中。在一个德国学者的身上,我看到了魏晋风流。瓦格纳先生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那么专注和生机勃勃的模样,以至于当我听到他辞世的消息时,极其震惊。犹记得那天恰逢我回北京开会,下了飞机,坐在开往北大方向的出租车上,突然看到这个消息,我把头抵住车窗,望着窗外北京特有的蓝天,默默地流泪。
我自本科起就认识王德威老师,先后两度赴哈佛访学端赖其不遗余力的支持。当年他与陈平原老师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指引我初窥“北京学”的堂奥,因缘际会,后来二人都成了我的导师。2007年在王老师有关“抒情传统与现代性”的北大系列讲座上,许子东做过一个很妙的比喻,说陈平原治学,如在一块领域内深耕一棵树,枝繁叶茂;王德威则如将几朵天南地北的花插在一处,花团锦簇。十年前在哈佛时与王老师对谈论文,他眼中常闪烁着光芒,提示我灵光一现的洞见。王老师曾戏言,到时候你最终做出的博士论文,人家一看,一半像陈平原,一半像王德威。这当然是玩笑话,我曾很长一段时间都担心自己糟蹋了《来今雨轩的过客》这个好题目,后来又渐渐释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之“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我的书稿同样带入了自身对于北京的理解和感受。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个人气质是偏于“现代”的,这大概也奠定了我看待北京的眼光。在台湾访学时的指导教授刘人鹏老师曾对我说,她对北京最失望的是什刹海一带,惋惜商业因素的引入破坏了南锣鼓巷、烟袋斜街这些老胡同原汁原味的北京风情。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原汁原味”的老北京何尝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读书时我曾选修陈平原老师的城市研究课程,最后一堂课要求我们借一张图、一首歌或一个小物件之类诠释自己对于北京的印象。我选了一张照片,是烟袋斜街对面一条不知名的小胡同——很不起眼的破败小巷,深处却张挂着许多朋克风格的招牌,上书英文字母Tattoo(即刺青),衣着入时的摇滚青年与推着代步车的老大爷,相映成趣。非常奇妙的拼贴,却又那么自然而然,毫不生硬。我认为,这正是北京的神奇之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古董,我们也不应把它作为一个静止的博物馆;它既不是完全旧的,也不是完全新的,而是充满了包容与张力,其老躯壳里很可能流淌着最新鲜的血液。本土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彼此相安无事,各得其所。这也是我理解近代北京公园的起点。 做北京公园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一种无人关注也无人对话的状态下,是陈、夏两位老师一直笃定地支持我在城市研究的路子上走下去。十年过去,倏忽之间,“公园”这个议题在疫情的语境下又被赋予了时代的意义,引发公众媒体的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共空间之于城市、之于生活的意义。2022年5月,在广州“一席”的讲台上,我应邀讲述北京的公园故事,我从“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以北海公园为主题的歌谈起,最终又归结到北海,谈到公园象征着一种日常生活的秩序,城市空间因人而被赋予意义,希望我们的城市能早日恢复日常秩序,我能再去北海上荡起双桨。当时疫情正盛,据说,许多观众当场潸然泪下。而我在7月底按计划赴美访学之前,也确实暂时没再能实现回京探访师友以及泛舟北海的小心愿。
而今,我远在波士顿,重新审定我的书稿,在想象中重游北京,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世界人”的乡愁。当康有为日夜坐于异国的公园之中,写下“故国园亭梦似归”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当梁启超提出“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污下”的时候,公园对于他现代国民、现代国家的理想又意味着什么?学术研究始终是与生命体验紧密相连的,对于学术的接受与理解亦然。学术从来不只是纸上的、客观冷静的文字,它折射了过去的人们的生活,也投射了现在和未来的人们的生活。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一书后记,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许革,张彦武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