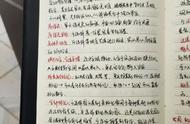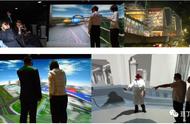马斯克谈这些话的时候,挑战的权威是NASA,他对火箭这东西做出的一系列操作,都是在向世人证明,过去60多年来,NASA的科学家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并没有违背物理定律。
有趣的是,时间退回到1962年,就在NASA成立第五年,肯尼迪总统公开发表演讲,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很简单,而是因为它很难」。这句话后来被称为NASA迈向月球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可以达成统一,把建筑行业推进新技术的现状归结为「很难」,而不是「不可能」,那么接下来我想讲的所有话,才算是有意义。
关于「难」,我想起最近经历的四件小事和一点点心得,先说给你听。
第一件事:难就对了做这行的媒体不算太晚,有幸在比较早期认识了一些朋友,大家各自努力,有不少做到了企业的管理层。
其中就有这么一位朋友,所在的公司在咱们行业也算数一数二,名字没经人家允许就不说了,在职位上做得很好,深得董事长的信任。这两年公司需要做一个重大的业务转型,开辟一片完全不同的市场,就让这位朋友带着一支年轻的队伍,出去做排头兵。
出去摸了几个月,大家回来跟董事长汇报。老板就问,大家这几个月感觉怎么样呀?
大家纷纷抱怨说,老板你可不知道,这市场太难做了,水太深、客户太难伺候、钱还不好赚。
老板笑了笑回答说:那挺好,难就对了。要是你们说挺容易*,那这事我的决定还就真错了,这么几十个年轻人出去一趟就能成,那证明商业门槛太低,干成了也没有护城河。
听他说这事的时候,我正好在读《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开篇给了25条真诚的建议,其中第16条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巨大的变革性机会,不要疑虑其他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你可能看到了他人没有看到的东西。问题越严峻,竞争就越有限,对问题解决者的回报就越大。

人们做一件事特别需要精神共识,共识越多、安全感越强,但有句话怎么说的?当隔壁大妈都来跟你聊股票的时候,赶紧抛。
机会是稀缺资源,事后的成就和事前的共识,很遗憾地成反比,而你只能选一个。
第二件事:赤脚的老板想让大家对一件事达成共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一起对这件事挑毛病。
前阵子有机会出差到上海,一位国际知名公司的老板,带着几位技术骨干做调研,核心的议题就是入场了建筑业数字化,遇到了些困难,事情怎么搞,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有幸作为一个见证者,被邀请到这个闭门会议里谈谈自己的观察。
八个人从下午聊到晚上,不知道从哪个话题开始,与会专家、连同这家公司的技术骨干,都对一个话题打开了话匣子,那就是工程建筑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搞数字化有多难。
你敢信,大家各抒己见,彼此认同,这个话题硬是聊了两个多小时。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在座的各位我比较年轻,斗胆问一句,咱们议题的方向是不是跑偏了?今天贵公司来调研,母题应该不是「多难搞」,而是「怎么搞」,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结果是「什么都不做」,那是不是有点太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后来在那位老板的主持下,我们总算是又聊了几个小时的方案建议。
那天晚上,这位老总执意要我坐他旁边,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酒过半斤,我问起原因,他说:「今天下午你说的对,我压根就不是来听困难是什么的,我想听的是解决方案。想当年创建这家公司,除了一脑门子的困难,那真是要啥没啥,如果听了当时那些说没戏的意见,现在还是一家小破公司呢。」
那晚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如果一家公司上上下下都是能敏锐地发现困难的聪明鬼,那它早晚完蛋。我们的每一个业务,都是在没有充分了解困难的情况下,边做边琢磨地做出来的。
第三件事:流氓与海盗这位老总的话,我一直没太理解,稀里糊涂真的行吗?
巧了,最近听了一期播客,是对高樟资本创始人范卫锋的专访,采访中范卫锋提了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他说,为啥总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因为书生太理性了,缺少莽劲儿,他们得把一切问题都分析清楚了,各种风险都规避掉了,再去做事情,等他们动手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他还自嘲到,我们干投资的也不能去创业。还没行动呢,先站在上帝视角一顿分析,市场上看一圈数据,再看看同行,哎不行不行,这个事情风险太大了,不能做。

范卫锋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说现在咱们回看,过去十年在北上广深买几套房的,都赚大钱了,对不对。但你回到当时那个时间点,去问高级知识分子,去问分析师,人家懂市场规律、懂欧美历史,直接跟你说,不行不行,千万别入局,这房子很快要降了。
结果呢,这些人还就真的没买几套房,那些赚到钱的,全是不认识知识分子和分析师的「莽撞人」。
这个段子印证了一句话,我在前几年认识一位互联网投资大佬说过的:在那个变革的时代,凡是做成事的,没有书生和秀才,全是流氓和海盗。
那书生干什么呢?等海盗把江山打下来了,书生们会去海盗那里上班。他们会很快忘记上一次不可能是怎样被打破的,然后对下一个「不可能」嗤之以鼻。
第四件事:和谁聚在一起范卫锋这个投资人做的事很有意思,他专门跟各行业里优秀的年轻人打交道,给自己的定位是长期影响这些年轻人,培养他们成为企业骨干和创始人,借着人的变化来参与时代的变化。
老范在这期播客里自嘲,说自己做了一段时间的抖音,失败了,他发现自己要讲的每个话题,都要经过仔细的推敲论证,可评论区里根本没人能听他把话说完,看了标题就开杠,团队的人也建议他,别详细论证,5秒之内咔咔直接上结论。
老范觉得这样太难受了,自己玩不来,就弄了一个叫「老范聊创业」的播客,一期40多分钟,把一个话题好好说透。结果做播客特别开心,抖音做失败了一点都不遗憾。为啥呢?
因为作为一个投资人,他需要通过输出内容,吸引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人——也就是那些他希望影响、甚至投资的年轻人。发到播客来听的,起码是那种肯花时间听你把一件事论证清楚的理性人,也算是先做了一层筛选,还真是遇到了不少良驹。
选择和什么人打交道,可以通过内容深度进行筛选,老范的这个说法,我特别认同。
前段时间在重庆见了个朋友,他问我,BOX搞了这么久了,你们看到行业里有很多问题,甚至有很多黑幕,只要你写出来肯定有流量,又没人管你们,为啥你不讲那些很扎眼的坏事?
我说:讲坏事流量多,情绪密码嘛,这我知道。但咱这圈子本来就人不多,我爆个料搞来几万的阅读量,拿出去也真不算啥能带货变现的大流量。我得问自己,然后呢?然后来关注的全是跟我一起喷行业的人,那这些人我能联合他们一起做什么事呢?
当一群人对某件事的共识,建立在「这件事不行」的时候,当大家讨论的结论,集中地指向「什么也不做」的时候,这样的流量我还真是不要也罢,还不如联合少数正经想做事的人,走得更远吧。
悲观者往往正确,乐观者往往成功。我更愿意把宝压在乐观者身上,与他们同行。

在讨论这段短视频的时候,秦明还在群里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包括BIM在内的任何技术都不应该被攻击与批判,只是可能没有放在合适的位置与所处的时空。被攻击的对象本质上只是不符合个人利益或当下的潮流。当建筑业没有BIM,就像汽车产业没有BOM,那大众谈数字化变革可能再会谈什么话题呢?显然很难找到了。
判断大变革时代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新的组织是否不断诞生,央企层面的中央企业联盟很多,国央企旗下新建的组织就更多了。往往塑造这种新的组织就给大众提供了很多机会。
你说短视频里的观点和秦明的观点,哪一个见识面更广、背后的人生经验更丰富?不同位置的你可能有自己的判断,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更愿意与后者做同路人,因为前者在一起做事的可能性为0.
正题:真正的警惕好了,这四件事讲完,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我来说说我的想法。
开头提到,我想对那些把这段视频发给我、问我怎么看的小伙伴说,我不想抬这个杠,逐条反驳他分析的对不对。
人家讲的没啥不对的,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另外一件事。
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有人针对我们的「饭碗」提出了质疑。
我曾经问ChatGPT,「BIM技术的普及存在哪些困难」,结果它回答了5条,可以说句句戳中要害。咱们今天聊了,能发现困难,是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的年轻人都能做到的,这事不值钱,在AI面前就更不值钱,人的价值在于能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