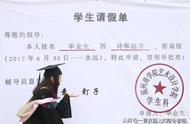汉语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一直都知道一笔一划,宛如图画,又似密码,形状千变万化,音韵也是波澜起伏。
叠韵词、双声词,读来像音节一样优美。
叠韵——韵母相同,比如“窈窕”淑女;双声——声母相同,比如“参差”荇菜。
如果把双声词延长再延长,变成一整个句子都是同一个声母,就成了古代的绕口令——双声诗。
它还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结巴诗。
来,一起跟我读。

花间鼻祖温庭筠,出了名的才思敏捷,据说叉一次手就能写出一句诗(一韵)
。所以,除了“庭筠”“飞卿”之外,他还有个不怎么美妙的外号叫“温八叉”。
写双声诗这种事对他来说,真是太简单了。
这首诗的颜值看起来非常不错,一如“玲珑骰子”“小山重叠”“蕊黄无限”,但是读起来么,大概就像是一盘色香俱全,但是味道诡异的菜吧


“双声诗”这样的体裁,比起诗词,更像是文人之间无伤大雅的游戏,既然是玩,怎么少的了“老顽童”苏东坡?
苏轼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看到一句话:玄鸿横号黄槲岘。
意思是,黑色的大雁在岘山上空,徘徊鸣叫,满山的槲叶,摇落如金。
纯天然的双声句让苏轼脑洞大开,对曰:皓鹤下浴红荷湖
这十四个字用宋代的语音读出来,都是同一个声母,可谓宋代版的红红火火恍恍惚惚韩寒会画画。
在座众人鼓掌,苏轼哈哈大笑,乘兴又写下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