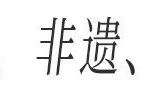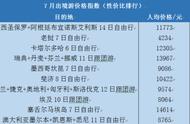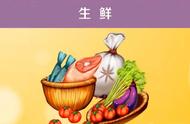江子
【编者按】: 一把油纸伞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作者江子在四川泸州发现了一个叫做“分水岭”的小镇。它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处,以盛产油纸伞闻名。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里拥有大大小小上百家油纸伞生产厂,从业人员多达上万人。然而,当机器生产开始普及时,手工制作开始失去了活力。
虽然油纸伞业已经萧条,但在作者眼里,油纸伞已经成为了另外一种存在——它的文化意义没有消失,它是文明的使者,是中国千年古文化的一部分,更是它改变了泸州的气质,让泸州风情万种。
泸州只是作者江子行走的其中一站,在《去林芝看桃花》一书中,他步履不停,前往浙江、广东、四川、新疆、云南、西藏、福建、台湾、江西9个地方,以自然风物为切入,娓娓道来与之息息相关的奇闻轶事,如浙江的“双龙六帖”“梅雨潭”、新疆“赛里木湖”、西藏“林芝的桃花”、福建“五店市的马”、江西“瑶里的月亮”“丰城的窑”等等。
作者笔触细腻柔美,内容丰盈饱满,不止是单薄地吟哦风景,而是以风景为线索,寻访其背后隐着的人、物与事,读来引人入胜。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书中“泸州的油纸伞”一章,一起走入这个神秘的边远小镇,了解油纸伞的前世与今生。
泸州的油纸伞
同大多数中国当代乡村集镇一样,位于泸州江阳区东南部的分水岭镇,是个看起来人气并不旺的地方。据说它曾是川、黔、云三省间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可我到达时,看到的是一条长长曲折的老街两边,店铺要么店门紧闭,要么懒洋洋开着的光景。街上既看不见人问价,也少有人走动。只有几家饮食店,门口的炉子冒着热气,炉子上的大锅里都煮着大块的豆腐。正是中午时分,店里三两人吃着,也不太说话。
我们走在街道上,总算让街道有了点人气。可这街道上仅有的本地人对我们的到来并不讶异,我们经过时,他们只是向我们投去匆匆一瞥,依然低头做着自己的事。偶尔有一两条狗躺在地上,似乎连睁眼看看我们都觉得费神。
这个集镇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植物长势凶猛。街道两边常常是巨型樟树,枝叶丰饶如巨大伞盖,树干要八九人才能合围,以为是长了五六百年才有的规模,一问才只有一二百年的树龄。从集镇往四周望去,青山环抱,色如新漆,似乎生命的喧响无所不在,再悲伤暗淡的灵魂都会如沐春风。
然而寂静的山沟可能是凤凰的故乡,表面如此冷寂的分水岭镇也会有风流妖娆的一面。当当地朋友领着我们转入了一个逼仄巷子,走进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子时,我们看到了与老街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分水岭镇不一样的风景。 视觉中国
许多人在忙碌。他们有的在用机器把木头裁成棍条状,有的忙于在木棍上凿细小的洞,有的在木棍上装上木条,形成伞骨,有的在伞骨上缠上丝线。有的呢,往伞骨上拼贴有图案的纸。还有的,往纸上涂上糨子……我不能详尽地叙述他们的工作,因为我的目光所及,他们工序复杂,分工精密,指间的动作细微谨慎,有着与机器生产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和耐心。
他们都是一些中年男女,与我在老街所见的本地人有着一样的朴素穿着。他们也与老街上的本地人一样无声,可他们有着同老街上的人们的慵懒闲散不一样的专注、静穆。他们的表情是深远的,好像在他们的心里装着一个远方。那个远方,叫作传统。——那是一种叫作油纸伞的古老制作传统。
你该知道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边远小镇分水岭镇,是中国汉文化符号之一——油纸伞的故乡。
那个面积巨大的百年老宅,就是全世界瞩目的泸州油纸伞的制作工厂。

泸州分水岭镇,以生产油纸伞闻名。 视觉中国
相传伞是鲁班的妻子发明的。
木匠鲁班每天都要出门工作,常被雨淋。鲁班妻子从门外的亭子造型得到启示,就用竹条做成了一个像亭子一样的东西,用兽皮搭在竹条上面,下面用一根棍子撑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伞。后来经过鲁班改造,伞成了收拢如棍、张开如盖的物件。
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人们借此改进了造伞技术,发明了在伞纸上刷桐油用来防水的油纸伞。
伞是寻常之物,可做伞却是个对原料和技术要求都十分高的活计:要能撑数千次不损坏,油纸被雨水反复浸泡能不脱骨,伞顶在暴风中行走能不变形。从选原材料到成伞,要一百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技术严格的质量标准。

制作油纸伞 视觉中国
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分水岭镇是个天然适合做油纸伞故乡的所在。那里植被丰茂,到处是适合做伞托的通木,深山里的老楠竹韧性大,弹力强,非常适合做抗大风不变形的伞骨。竹木又是做油纸伞的纸最好的材料。桐油呢,印刷精美图案的石墨呢,都可以在山上取材。
早在明末清初,分水岭镇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资源优势,开始研究油纸伞的制作技术。几乎是同时,泸州人开始生产日后让泸州闻名遐迩的泸州老窖。
分水岭镇人上山挑选最好的木头和老楠竹。分水岭镇人在经过防腐处理的木头和竹子上钻孔、拼架、穿线,精心布置用于抵挡雨水的各种小小的机关。分水岭镇人在纸上画上最好看的图画——在这张圆形的、与天空对话的纸上,分水岭镇人展开自己的想象,画上脸谱、山水、花鸟,画上对生活的赞美与祝福,并给纸涂上最好的桐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