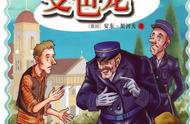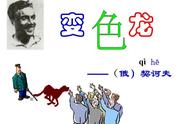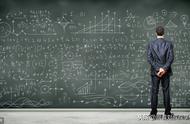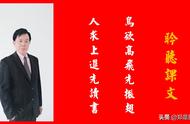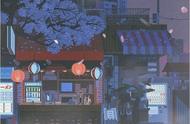“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再上那儿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既然普洛诃尔说这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的狗,”普洛诃尔接着说,“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他哥哥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小猎狗,他哥哥却喜欢。”
“他哥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蔑洛夫问,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
在《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每次听到“群体”中某人的话,都会转变一次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决定,会触及到权贵人士的利益。普罗诃尔是将军家的厨子,相对于奥楚蔑洛夫而言,不仅是“群体”中的一员,还是权贵的象征。普罗诃尔作为狗身份的证明人,原本可以一次性交代清楚狗的主人是谁,却偏偏要断开、分成两次说。
这样的断裂,在小说中称为“话语的断裂”。狗被普罗诃尔证实不是“将军的狗”后,奥楚蔑洛夫欲*死这条狗;当普罗诃尔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时,他又马上堆了满脸的笑容。在普罗诃尔“话语的断裂”下,主人公奥楚蔑洛夫见风使舵、虚伪逢迎的形象也得到了突出。
作家通过笔下人物“话语的断裂”,本来可以一次性说清,却偏偏要断开,分成几次。这样不仅使情节变得跌宕起伏,还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其实,《变色龙》中的“群体形象”,即使放在现如今,也同样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我们既是“群体”的一员,也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行者。在《变色龙》中,作者通过对“群体形象”的描写,讽刺了沙皇专制统治下,社会的冷漠和“群体”的麻木。
而现实中,2岁的小悦悦在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辆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却视而不见、漠然离去;山西黑砖窑事件中,黑砖窑老板,让残智人员免费做苦力,周边的农民也都漠不关心;浙江一中年男子欲跳楼,围观人群非但不劝阻,反而大呼:“你跳吧跳吧,想想你也不敢跳。”
《变色龙》中,我们生气“群体”的麻木不仁;现实社会里,我们却“模仿”故事中的人物,将冷漠搬到了生活中。
有关实验显示:施助行为与人口的密集度有关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场所,人们往往会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这就导致了许多人认为,该做的事情别人会去做,或者认为既然别人不做,那么自己也就不必或者不能做。
这也就是所谓的“从众效应”及“责任分散效应”。因为别人都不管,所以我也可以保持沉默。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冷漠。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境遇,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变色龙》中,一个小人物郝留金,一群无聊的看客,演绎了一段可怜的遭遇。现实中,一次从众的决定,一个冷漠的态度,不仅会让无数个悲剧重演,也有可能会将自己推向悲剧的主角座椅上。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其实,郝留金的悲哀,不在于狗的横行,而在于“群体”的沉默。因为渗入“群体”骨髓的麻木与冷漠,是比“刀”还要锋利的利器,“*”人于无形。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以麻木不仁的态度生活。既然活在当下,就不应选择冷漠。事实上,“群体”不该是坏事情的推波助澜者,“群体”应该懂得守望相助的道理,应该学会用温暖和真情,感动世界、温暖人心。
正如萧楚女所说: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
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不再选择冷漠,而是选择温暖,那么整个“群体”就自然会变得温暖,生活也不再只剩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