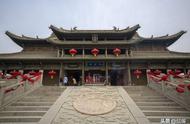每次我给新来的通讯员讲新闻写作课时,都会提到新闻的五要素,但我说的不是国际上通行的“五个W”,而是自创的“五个H”,即5个“何”:“何时、何地、何人、何因、何果”,我都觉得“何”比“when/where/what/who/why/ what/”来得更简洁、更典雅、更中国化。
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都喜欢用“何”,而不愿意用它最通常的同义词“什么、哪里、为什么、怎么样”,在我眼里,“何”有种与生俱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胸有成竹的气度,甚至还有一点阳春白雪的气质。
虽然“何”由“可”和“人”组成,但有时对听者来说,一点都不可人,特别是在反问的时候“何必呢?”“何尝不是?”“何苦呢?”“究竟为何?”“与我何干!”那种自以为是、以他为非的不屑感溢于言表,但对说者来说,气势磅礴,有一种洞察对方短处的痛快!
很多没感情色彩的词,一与“何”搭配,顿时气韵生动,气势非凡。“奈何”“缘何”“何啻”“若何”,虽然只有两个字,也是自带气场,元气充沛,而那些与“何”相关的成语或俗语,比如“其奈我何?” “何罪之有”“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是情绪饱满、语气洒脱,甚至说话人的神态都恍然生动,呼之欲出。
虽然现代人都习惯说大白话,但很多人对“何”字还是情有独钟,言语中使用“何”,似乎不仅是为了言辞的简练,还为了那种文绉绉的感觉。“何物?何人?何意?何去何从?”,比之“什么东西?什么人?什么意思?哪里来去哪里?”对风雅之人来说,感觉是云泥之别的。
“何”经常与“以”连用,意思是“以何”,表示“拿什么”,是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没有或不能的意思。如,“大恩大德,何以回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言简意赅,读之铿锵,思之有味。

“情何以堪”如前几年的“洪荒之力”一样,是现在用得比较滥的一个词,年轻人经常以玩笑的口吻来表达“让我情感上怎们能承受呢?”,但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东晋大司马桓温对时光流逝所发出的感伤“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桓温北伐,经过金城,见年轻时所种的柳树都已经十围了,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树都长这么大了,人就更不必说了,岁月无情催人老,英雄迟暮空怆然。

因“何”有自带流量的强烈感情,特别适合排比,故文人喜欢用“何”来铺排文辞。
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铿然写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两“何”连用,气势磅礴,充满了必胜信心;
杜甫《石壕吏》“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个“何”引出战争致老妇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
《木兰诗》中的“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朗朗上口,可以倒背如流;
魏晋名士嵇康看不起慕名前来拜会他的钟会,手中打铁不停,不置一词,直到钟会悻悻而去,这才漫不经心吐出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闻而去?”,以“何”发问,既有傲慢,又有戏谑,钟会虽然人品不咋地,但才气和风度还是和嵇康棋逢对手的,随即不卑不亢对答曰“闻所闻而来,闻所闻而去”,这也是后人关于名士风度津津乐道的传神场景之一。

何,作为姓氏,可圈点的名人大家没法和那些浩若星辰的大姓比,但何姓出了一个美男子,那就是留下“何郎傅粉”典故的正始名士何宴,何宴如果容貌俊美、面容细腻洁白,倒也不值一提,关键是他的才华出众,崇尚清谈,开一时风气之先,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

我比较喜欢的名字是诗人何其芳。本来“何其”就是一个感叹词,多么的意思,何其芳,那是多么的芬芳!
喜欢诗词的人都知道有个词牌叫《何满子》,但不一定知晓这何满子本是一名善歌的女子,不值因何事得罪了权贵,临刑之前,哀歌一曲,悲愤凄凉使得天地为之变色,歌声竟然传到懂音律的唐玄宗耳边,玄宗惜才,降旨赦免了她的死罪。此后,《何满子》就成了悲歌的代名词。以它为词牌而作的词大多是伤春悲秋、离愁别绪、感叹人生光景的,最著名的当属张祜的那句“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了。
“何”作为疑问和感叹词,都极容易引起人的情感波动。“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臣子恨,何时灭?”“春花秋月何时了?”“虞姬虞姬奈若何?”
而此时,无论是季节时令还是我的年龄,可以是寒冬正浓,而自己半生蹉跎,一事无成,纵有千种风情,万种心愿,又将如之奈何?唯有“一声何满子,垂泪文字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