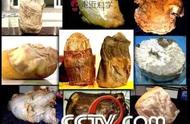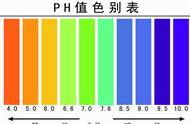众所周知,陶渊明是一位生于乱世,却豁达、乐观的人。因为这份豁达,所以他在面对生死时,总能抱着一份“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的态度;因为这份乐观,所以他在面对生活时,才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得。我们喜欢《桃花源记》,不光是因为它给了我们自然的美景,更因为在《桃花源记》中,我们能读出陶渊明的豁达和积极,能为陶氏的人格之美而震撼。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末期,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小发奋学习的他,怀揣着“济天下苍生”的伟大梦想,但他势单力薄,直到死也没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即便如此,陶渊明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所以,他选择了归隐。文中“不足为外人道也”、“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就都体现了陶渊明的避世思想。
但,陶渊明的避世,绝不是逃避。正如布洛赫所说:“乌托邦即人所渴望的对象,在现实世界的空缺。”陶渊明从不消极逃避,他只是在认清了现实后,通过对理想社会的塑造,抗议和攻击现实的腐败和黑暗罢了。
因为一个对生活消极怠慢的人,又怎么有心情看花、看树呢?如果不是出于热爱,又怎么会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追求和向往呢?
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道家一贯的精神,则在于“以天下为己任,即使自身粉身碎骨,也要还庙堂一个清明。”
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身处乱世,也明白官场的尔虞我诈;朝廷的腐败无能,但是,他仍能以天下百姓的平安、喜乐为己任,立志建立一个“平等、安全、自由”的完美世界,做到了一个“英雄”应该做的事情。而这样的“英雄”所为,也和道家的思想不谋而合。而这份不谋而合的思想,则表达了陶渊明积极、豁达的人生观。

在《桃花源记》中,我们读到了陶渊明独具匠心的四“美”,也通过各个“美”,分析了这篇文章备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众所周知,桃源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也是一个完美的“乌托之邦”。很多人心向往之,但也有很多人对这个“乌托邦”颇有微词,认为它不过就是“空中楼阁”,毫无用处。
但事实上,这个“乌托邦”并不是一拍脑门的无稽之谈,也不是无可奈何的隐世逃避;而是陶渊明在影射政治后,想要*的一个理想世界,它饱含了作者对现实危机的反思与思考。
在桃花源里,乡民们“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他们活得自给自足,他们平等自由,不被压迫、不被苛待。是因为百姓们受够了“战乱纷争”的折磨、“分裂割据”的摧残。在桃花源里,无论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还是“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的乡土日常,说到底,都是陶渊明和百姓们的内心渴望。
保尔·利科曾这样解释“乌托邦”:“我们仅仅承认乌托邦是一种被书写的类型。乌托邦从初始的一种文学类型构成,就明确了自身的空间。”
也就是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将以“乌托邦”命名的理想社会创造了出来,“乌托邦”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并且也明白自己代表了大家内心的渴望。而这份渴望诞生的背景,其实就是源于混乱的现实危机。而《桃花源记》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份藏在乡土背后的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桃花源记》备受推崇,以及值得大家阅读的原因。
所以,虽然有些人认为,“乌托邦”有着虚无、逃避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乌托邦”同样有着展现人类面临危机与困境,帮助人类反思的一面。因此,它的存在是有必要的,正如芒福德所说:“如果没有其他时代的乌托邦,人类可能依然赤身裸体,悲惨地生活在洞穴中。最先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座人类城市的是乌托邦人”。总之,我们对“乌托邦”不该是追捧或是批判,而是应该全面、理性地看待它。

其实,不光是“乌托邦”,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我们不该只看到一面,就妄加揣测或是评论。阅读文章如此,做人亦是如此。
在《桃花源记》中,我们不仅读到了陶渊明遣词琢句中的“精美”,也体会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更明白了看问题,所应该具备的全面性。紫陌不禁感慨,一篇不足400字的文章,竟能写得如此精彩,难怪时隔千年,大家依然会对它爱不释手。所以,还等什么呢?要不要再来一起读一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呢?看看今天的你,是否又会有新的感悟呢?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桃花源记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