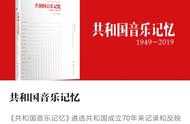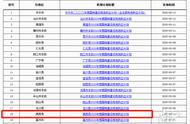当乐曲结束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如痴如醉。张丕基看到了李谷一眼中的泪花:“你哭了!”李谷一回答:“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
而导演马靖华竟然忘了发出指令关掉录音机,以至于把张丕基和李谷一的这两句对话也录了进去。直到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保存的歌曲《乡恋》的母带中,仍然保留着这两句话。
多年后,李谷一告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记者:“歌曲《乡恋》所述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艺术境界,歌曲所倾诉的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乡思打动了我,所以演唱起来非常动情,一气呵成。”
当年的最后一天,即1979年12月31日的晚上8点左右,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全国的观众按照惯例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观看美国科幻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然而短暂的广告过后,大家没有等到《大西洋底来的人》,却等来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而《乡恋》这首歌也随该片一起播出。

有些观众没有看到心目中的“麦克•哈里斯”,失望之余而离开了电视机,从而错过了一个见证历史时刻的机会。而仍在坚守的观众,当听到李谷一那带着浓浓乡愁的歌声出现时,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被她的歌声所感染。听惯了她明丽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突然听到她“含着嗓音唱歌”,大家既惊讶又惊喜。有一个女工小声说,“李谷一唱歌怎么跟说悄悄话似的。”她的话无意中道出了这首歌“轻声”、“气声”的特点。
放眼全国,上海总是站在时尚的最前沿。而随着《三峡传说》的播出,上海人也是最敏感的。
就在第二天,即1980年1月1日元旦,上海的《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里面的歌曲十分优美动听,得到大家的喜爱。之后,人们便四处打听和寻找这首歌。
就在人们四处打听和寻找这首歌的时候,1980年2月,歌曲《乡恋》入选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栏目。当时的《每周一歌》栏目,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18点到18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的影响力特别大,耳目一新的词、耳目一新的曲、耳目一新的配器、耳目一新的演唱,霎时让《乡恋》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来。
与此同时,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把《三峡传说》中的配乐、插曲,包括歌曲《乡恋》录制成唱片、磁带公开发行。短短的几个月,唱片、磁带销量数以十万计,无论是在热闹喧嚣的大都市,还是小城镇,《乡恋》迷人的旋律和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总不绝于耳、“声声”不断。张丕基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排队买东西时都在哼唱这首歌。
而有谁知道,随着《乡恋》的流行,李谷一却从“歌坛新秀”一下变成了“黄色歌女”,演唱《乡恋》却变成了罪孽,以后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
04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一般来说,歌曲的词要写得很革命,曲要写得很响亮,而描述思乡、离情的歌曲基本没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像“恋”、“美梦”、“情爱”这类表现人们心灵最软处的歌词,几乎没有音乐作品去触及;而在歌曲《乡恋》里,却把这些让当时的人们脸红心跳、如春心萌动的词汇都一起在这首歌中迸发了出来。此外,在谱曲时,《乡恋》也不再是过去激情的四二、四四拍的机械硬节奏,大量的休止符、切分音被不断运用,“探戈”的曲式以及柔美婉转的旋律使《乡恋》在当时的歌坛让人耳目一新。而在演唱中,李谷一更是加入了“轻声”和“气声”,情到深处的抽泣腔更加重了依依不舍的离情,使人们第一次听到一种类似于耳边娓娓倾诉式的歌唱,这与当时主流的“高强响硬”的演唱方式是大相径庭的。

在演唱这首歌时,李谷一的声音飘渺迷离,旋律优美深情,她在演唱中运用了“轻声”与“气声”结合的唱法来处理,再加上她那良好的气息支撑与咬字的精确与松弛,仿佛让人们身临其境。所以,《乡恋》这首歌一经播出,就像一股清爽的风,吹拂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让听众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美妙享受从而引发出强烈的感情共鸣。
而这种唱法,也成了后来内地流行唱法的先驱——《乡恋》开始风靡后,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唱歌时模仿李谷一轻声细语的样子。会唱的人用气托着声音唱,不会唱的人则喘着气唱,这也成了最初通俗唱法的一个最浅显的标志。而许多更年轻一点的歌手,又从李谷一的创新中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创新;更有些人专门模仿李谷一的唱法,以至于社会上经常听到“李谷二”、“李谷三”之类的称呼。所以,许多年来直至现在,李谷一是中国音乐界一直公认的内地“流行唱法”的第一人。
在当时,李谷一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乐道的一个名字。而在演唱歌曲《乡恋》时,因为在唱法上有了这一小小的创新,更使得李谷一的歌声沁入到广大群众的心底。但与此同时,这种唱法也招引来一片窃窃私语和各种非议之声。有不少的人都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走了板,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有不少好心的人出来向她发出警告:“应当止步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
于是,歌曲《乡恋》因为“新”的唱法而遭到了非议。因为按照当时歌唱类型的划分,这首歌的唱法,既不属于美声唱法,也不属于民族唱法,而是更倾向于港台的那种流行唱法,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是碰不得的。于是批评之声也随之而来,而非议最多的,就是李谷一所采用的轻声、气声唱法。
说到这首歌的演唱方式,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李谷一用的是“气声唱法”,一直以来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宣传中,一提到歌曲《乡恋》,就说李谷一用的是“气声唱法”,而李谷一却很认真地纠正说:“诸多听众都说这首歌用了气声,其实没有什么气声唱法,就是轻声,或者可以说半声。”
录制这首歌的时候,适逢国家刚刚提出改革开放的决策。身为一个歌唱者,李谷一认为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响应改革开放创新的召唤,也为了使这首歌更加感人肺腑,根据旋律和歌词的走向,我就尝试着用半声演唱,因为全声太过生硬了。”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李谷一每次举例说明气声唱法的时候,她提到《绒花》、提到《妹妹找哥泪花流》、提到《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及《知音》等歌曲的片断,但她从来都不提《乡恋》,因为《乡恋》用的不是气声,而是轻声。
本来,在此之前,李谷一已经是那个时代最有大众知名度的歌手之一;而她为多部电影配唱的主题歌、插曲,更是为广大观众、听众所喜爱,以至于在电影界有“每片必歌、每歌必李”的说法。这种由李谷一几乎“垄断”电影插曲配唱的奇特现象,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
在1979年上映的故事影片《小花》里,李谷一演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还有电影《泪痕》的主题歌《心中的玫瑰》等歌曲时,就大胆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这一突破,使我国的歌坛立即为之耳目一新,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荡着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那舒缓的轻声和颤动的气声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虽有批评者认为此歌曲唱法不妥,但碍于《小花》、《泪痕》等电影属于反映革命战争的红色革命范畴题材,虽然歌曲的唱法有些创新,反感者却不好说出更多的话来,只能暗自嘀咕,无法公开指责、批评。
而此种唱法后来运用到《乡恋》中时,却情形突变。
05那些平时对李谷一“气声”唱法嫌弃和看不惯的人,由于对她在电影歌曲配唱中频繁使用气声唱法已经“忍无可忍”,这时就更是怒不可遏了。那郁积已久的李谷一的唱法问题,在新旧观念、新旧隔阂、新旧矛盾、新旧分歧的碰撞下,统统在这首歌曲上爆发了。尽管李谷一一再坚持在《乡恋》中运用的是“轻声”,而不是“气声”,但是那些人还是把《乡恋》与“气声”唱法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于是一时间,电闪雷鸣,风雪冰雹,一齐向她袭了过来——
198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在讲话中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港台有个邓丽君,内地现在有个“李丽君”。
1980年2月起,《北京音乐报》辟出专栏对歌曲《乡恋》进行讨论,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虽然名义上是“讨论”,但之后便发展为批判。而仅在2月至3月间,就连续发表了11篇文章。
1980年2月10日,距离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仅剩不到一周的时间。《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了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评电视片<三峡传说>中的一首插曲》。文中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指的就是《乡恋》。李谷一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应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首歌确实是一首‘情歌’,但它表现的是对故乡的‘情’,对故土的‘情’,而不是男女之情的‘情’。”
在这篇文章里,“莫沙”全盘否定了《乡恋》的创作,称歌曲《乡恋》的创作者们“热衷于搞邪门歪道,是安于模仿的懒汉”、“缺乏民族风格,缺乏特定的时代特点,格调和情趣完全不对头,相当的不协调”、“带有浓厚的殖民味道”等等,整篇文章充满了“*气”。如果说还有什么客气之处,只不过是没有点马靖华、张丕基、李谷一三个人的名字。
《北京音乐报》继莫沙的《毫无价值的模仿》后,又接连几期几乎整版刊登对李谷一演唱《乡恋》的争议,如《歌唱小议》中说,李谷一每段歌词要用四、五次“大喘气”,比如“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一句里就有“大喘气”三次之多,叮叮咚咚的电子鼓敲得莫名其妙,等等。
于是,报刊上开始大量刊发对《乡恋》的批评文章。

1980年三月号的《人民音乐》把主题定为《探讨当前音乐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十多位音乐界名家名人对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思潮,从创作、演唱、社会影响等不同角度谈认识和感想,自然是以批评为主,虽多为不点名,但目标明确。
此后,在持续三四年的时间里,围绕《乡恋》的全国性大讨论始终热度不减。
这时候的争议、批评已经与电视片《三峡传说》的内容无关,而是将李谷一与《乡恋》划为等号——《乡恋》就是李谷一,李谷一就是《乡恋》。
对《乡恋》这首作品,有的说它“娇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它“格调不高,在气质情趣和人物的品德等方面都不够健康”;有的说它“很像目前海外歌星们演唱流行歌曲的路子”;也有人说“这首歌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是灰暗的、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就这样,一时间,《乡恋》成了“大毒草”,而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歌唱家”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成了一个不需要签证,一夜之间就打入祖国大陆的“李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1980年3月25日,针对各种批评和打压,李谷一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还是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邓丽君跟我是两码事,她唱她的,我唱我的,她唱的方法跟我完全不一样。”然而,那些反对她的人并不买账。
1980年4月,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了“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史称“西山会议”。在会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
张丕基提到这位负责人的发言时,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气腾腾”。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唱”。
李谷一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她在会上反驳了一些横加在她身上的“罪名”,并且提出了声乐技术创新的主张和思路,并且一再地声明:“我在《乡恋》中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
可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她的辩护,而且说得很具体:作词和作曲的问题都不大,毛病就出在唱法上。甚至有人劝李谷一改变唱法,重新录一版《乡恋》,却遭到这位倔强的湖南妹子的拒绝:“如果重唱重录,改变唱法,那李谷一就不是我了,那首歌也不是《乡恋》了。”
而据张丕基回忆,在这次会议之前,某省的电视台还曾约他作曲,后来一听说“西山会议”的情况,就毁约了。
由于受歌曲《乡恋》的牵连,作曲家张丕基以及为故事影片《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作曲的王酩也受到了批判。善良的作曲家王酩曾劝李谷一“曲线救国”——先写检查应付一下,歌曲照唱。而直爽又倔强的李谷一却丝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观念:“因为我没错,我就不信唱首歌能把国家唱垮了。”
就这样,当几个高大的男人如王酩、张丕基等都写了检查后,看起来相对弱小的李谷一却依然“顽固不化,死不认罪”。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谷一的丈夫肖卓能不无担忧地对记者说:“要知道,李谷一当时的举动是多么悬呀!她真是豁出去了。”
而此后不久,1980年4月间,中央乐团的领导给正在外地随团演出的李谷一写了一封信,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就请她另谋高就,这里已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舞台了,只好请她找适合她发展的地方去。“就是说,如果再要继续这样唱的话,你就回湖南去。”李谷一回忆说。
在当时的舆论批评中对歌曲里面的打击乐也就是架子鼓也反响强烈,那个时候的架子鼓在歌曲中的伴奏还是很少有的。记得有个所谓评论家这么说:“歌曲没有革命斗志,听了容易使人意志消沉,喘着粗气,真担心上气接不上下气,还有那个架子鼓在间奏之间一阵乱敲,像在瓷器店里砸碗一样,噼里啪啦,像什么东西,糟踏了歌曲……”
06就在各大媒体对《乡恋》的批判、声讨声中,各级电台、电视台迫于压力,或者说是为了避嫌,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歌曲《乡恋》的播放,广大群众在此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再也没有从电台、电视台收听到《乡恋》这首歌。
而面对这些批评、责难,李谷一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没有更多的时间,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应付这一切,因为她实在是太忙了、太累了。
当时她所在的中央乐团实行的是半独立的经济核算,乐团的开支主要依靠综合乐队的演出收入来维持。所以,中央乐团每年都有一定的演出任务。而李谷一作为全国著名的歌唱演员,这时一直随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而演出的任务却异常地繁重。一年多来已经演出了200多场,甚至曾经有过50多天唱72场的记录。
据李谷一回忆:“那时候,尽管受着批判,还要保证团里的演出。1980到1982年期间,我每场演出必唱八首歌,观众要求返场,还得加唱四首歌,总共十二首歌,相当于一场个人音乐会,而且,经常一天要演两场。为此,在那两年当中,我的声带四次出血,但还要坚持演出。当时,为了保证演出,特别是到外地,团里派位医生跟着,每天要给我注射六至八针药品。”
除此之外,她还要给电影和电视剧配唱主题歌和插曲,几乎没有一点间歇。比如,就在为电影《小花》配唱插曲的前夜,她还在秦皇岛舞台上为观众演出。她的节目整整提前了2个小时,就是为了能够赶上火车返回北京。当赶到北京的家时,已经是午夜12点了。而她在第二天清晨8点就赶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录音棚。上午录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下午录一首《绒花》,第二天上午,又搭乘火车返回。下午6点钟赶到北戴河,7点就已经在舞台上演出了。
而在当时的1980年3月,正当全国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对歌曲《乡恋》进行批判的时候,她却在北京刚刚结束了演出,就一路南下到了江浙,48天里演出了45场。除了4月份在北京参加了几天的“西山会议”,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外地演出。几天前还在天津,而刚进入5月就又到了上海,接下来还要到沈阳、大连、西安等地,年末还要赶到广东、广西。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李谷一的身影。
与冷酷的打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观众对她的支持,全国各地的观众勇敢地站在了李谷一一边。巡回演出场场爆满,呼唤《乡恋》的声音更是震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