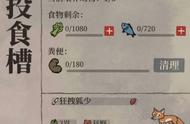▲ 荠菜馄饨,上海人的“心头好”。 图/视觉中国
上海人喜欢荠菜大馄饨,南京人还爱吃荠菜春卷。猪肉做馅,拌上荠菜,醇香与清新两种滋味,彼此成就开春的美好。等到了宁波,水磨年糕配上荠菜,又成为一道荠菜炒年糕,若是拌上香干、春笋、嫩豆腐,也是一道下酒好菜。难怪说江南人的春天,是荠菜做的。

江南的野菜,不只在舌尖上,更在舌尖之外,成就了江南的底色。
人们总以为江南这两个词,八分藏在杏雨春风的诗词歌赋里,殊不知,“城中桃李愁风雨”,江南人爱出门踏春、咬春,生活气象,要去山野之间的草根里寻。

▲ 初春时节,江南水乡的路边到处晾晒着新鲜的雪里蕻,等待时间将它们催化。摄影/罗军,选自《风物中国志·同里》
许多江南人都曾为野菜著书立说,可见兼济天下的精神。南京人朱橚(sù)写《救荒本草》,我们今天吃的众多野菜,大都在此书里;那个写了“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的高邮人王磐,还写过一本《野菜谱》,采集尝吃野菜多达52种,老饕汪曾祺读了,都直呼内行。
毕竟,匮乏年代,野菜是救命草,藏着生命的坚忍力量,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野菜还是一种能够出口创汇的重要物资,如今看到长辈们痴迷野菜,很多时候是一种过去的身体记忆。

▲ 荠菜与口蘑,春与冬的相遇。摄影/easonxin,图/汇图网
若是到了太平时节,野菜便摇身一变,透出几分江南人对待万物的细腻,所谓“不时不食”,野菜便是第一站,春光周而复始,野菜的味道,就沉入了江南细细密密的文化底色。如果某位江南名家,没留下以野菜为主角的名句或者桥段,仿佛就少了些什么。
苏轼带着蒌蒿与河豚同游;《红楼梦》里除了芦蒿炒面筋,还有宝钗和探春点名要吃的油盐炒枸杞芽;汪曾祺与周作人,也都对故乡的野菜念念不忘。小小野菜里,有对生活的深远寄托,想着带些野菜味的“莼鲈之思”,人生也便有了几分退路,更加从容不迫,意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