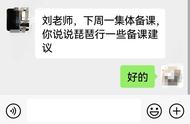概括来说,这一部分一是要求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比较,以显示两诗“在音乐描写上”的异同点,二是要求与白居易的《观刈麦》比较,直指白氏的“现实主义情怀”。
先说第二点。《琵琶行》的主旨如果一定要说“既是对自己不幸遭贬的伤感,更是对琵琶歌女晚年沦落的深深同情”,则可能显得勉强,与白氏的原意有较大的距离。而该案例将《琵琶行》“与《观刈麦》比较”,用意在表现诗人白居易对“下层百姓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及“封建官员的反思”,最终都落脚到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上,可能也是一个误置。

《观刈麦》诗作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自然没有问题;如果将《琵琶行》也揽入其中,则会引发麻烦。确实,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如同情疾苦、指刺时病,确实有一个较强的印证。但需要注意的是,诗人本人是将《琵琶行》列入“感伤”类,并没有把它置于“讽谕”“闲适”两类,即没有将所谓“兼济”之志、“独善”之义寄寓其中,而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以上相关引述,详见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第959-966页《与元九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虽然这一“牵”与“动”都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而收入该类的《长恨歌》和《琵琶行》确实也有一些讽谕性内容,但总归在“有感而发”,所流露的情感、情性要率然、真切些,而没有“讽谕”“闲适”两类明显甚至刻意的儒家“托寄”。

“现实主义”的《琵琶行》实际上是一种误置。“兼济”之志、“独善”之义不显,相反,正如乾隆所评:“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其音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又借明末清初学者唐汝询之口将情感寄托点白,说:“此宦游不遂,因琵琶以托兴也。言当清秋明月之夜,闻琵琶哀怨之声,听商妇自叙之苦,以动我逐臣久客之怀。宜其泣下沾襟也。”(乾隆御选《唐宋诗醇》,第467页,北京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也就是说,诗歌的着力点并不像诗人其他的诗歌诸如《观刈麦》《卖炭翁》等所表现的“他者”主题,而是借“他者”来表达自己的“逐臣久客之怀”。由此可见,“现实主义”的旨归在教学上的偏差是很显然的。

再说第一点。且不说关注诗歌中的音乐描写并非本次诗歌学习的重点,单说韩愈这首《听颖师弹琴》诗的阅读难度,即使配上注释,要让学生完整地理解,还是有不小的困难,怎么轻易就进行两诗的比较呢?假如不需要缀以学习的铺垫,学生像阅读浅显的现代文,看看即懂,那么,在逻辑上连同白居易这首《琵琶行》诗,安排如此课堂学习环节与步骤,岂不是煞有介事、装模作样,而实属不必么?再则,这首《琵琶行》里琵琶妙音究竟如何感受?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