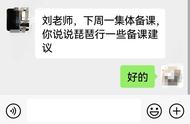《琵琶行》中所描写的“音乐”其实并不能直接被读者捕获,而需要一种想象,一种转化,需要通过另外的一种途径来解悟。在这一点上,艺术旨趣极高的傅雷先生,在给他儿子傅聪的一封谈及《长恨歌》与《琵琶行》的信件里,所涉及一些解说与相关方法,则对目前课堂困境的缓解有帮助。他说:

上星期我替(傅)敏讲《长恨歌》与《琵琶行》,觉得大有妙处。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韵。《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急切、迫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银瓶……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确起音〕,声势雄壮。至于《长恨歌》,那气息的超脱,写情的不落凡俗,处处不脱帝皇的nobleness〔雍容气派〕,更是千古奇笔。看的时候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分出段落看叙事的起伏转折;二是看情绪的忽悲忽喜,忽而沉潜,忽而飘逸;三是体会全诗音节与韵的变化。……(《傅雷家书》,第18-19页[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夜],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
傅雷先生音乐修养精深,他后面谈说《长恨歌》的三点读法,则完全适合于《琵琶行》有关音乐描写的部分。而具体到《琵琶行》诗,他举出了声韵的选择与情绪的关系,并敏锐地抓住了“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这一点,从形式着眼来进行一番讲解。他在诸如“断音”“休止”“明确起音”等处作了点拨,大致说明了音乐演奏的三个段落,至于演奏者或诗人情绪的变化,则是通过音乐演奏的快慢断续、高低起伏等变化而表现出来的。
现在不妨试着梳理一下诗人随音乐演奏的变化而伴随的情绪上的变化。

“嘈嘈”“切切”的乐音虽然急切,但在诗人的感受却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心底留下的却是快意(断音,即跳音,节奏欢快而奔放)。而“间关莺语花底滑”与“幽咽泉流冰下难”仍然是听众的幻化出的形象感受,而与之相对应的,既有音乐婉转流利时听者舒缓徜徉,也有音乐转入低沉缓慢时听者所感到的时间的久滞,这是音乐演奏与感受情绪同融的表达。接着是经过一段的休止,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聚集力量,也像是在调整姿态,总之,随后音乐再度迸发激昂的壮音“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然后便戛然而止,听者的情绪于是不能平静而久久沉浸在音乐的氛围之中。等好久再回过神来,才知道周围是那么安静——两只行船静静地停在江面,风平浪止,澄明的亮月正印在江心里。这对白居易来说,这种感受就是“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然而,这里的梳理还显得粗疏。究竟其契合度有多少,仍然需要根据白氏在诗歌中的暗示与他及他人在其它诗中的记述。当然,文学的表达手段是有限的,它只能是暗示,解会多少,则因人而异。不可否认,白居易很会享受当时种种歌舞,他是音乐鉴赏的高手。诗中说琵琶女“初为《霓裳》后《六么》”,所弹奏的曲调应该是一个大致记述兼听感。《霓裳》即《霓裳羽衣曲》,为唐玄宗所作的道教献祭舞曲,其情景可能拟绘于月宫仙子数百素练宽衣飘舞的情形。白氏很多诗中多次提到,可见他对这支音乐的迷恋程度了。作于白氏晚年的《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有细致的描绘,(间引施蛰存《唐诗百话》,第491-492页,上海古籍1988年版)其中“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引文见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第459页《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与“大弦嘈嘈如急雨”“大珠小珠落玉盘”至“铁骑突出刀枪鸣”所写的则较为契合。

再看《六幺》,是流行于唐宋的著名软舞。其舞姿柔婉飘逸,节奏先舒缓,后渐加快。白居易《乐世》诗曰:“管弦丝繁拍渐稠,《绿腰》宛转曲终头。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并自注:《乐世》,一名《六幺》。(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第810页《乐世》诗)而同为唐人的李群玉,在其《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二首》诗里对这种软舞也有比较完整的记述:
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翩如兰苕翠,宛如游龙举。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苕。
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堕珥时流盼,修裾欲朔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见《四部丛刊集部•李群玉诗集》,上海涵芬楼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