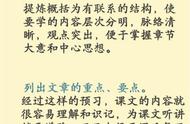木心
长到十几岁,木心结束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来到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他离开后,茅盾书屋很快毁于战火之中。
在上海念书时,虹口区的虬江路是木心的常去之地。日本人战败后踉跄回国,留下堆积如山的物件用品,包括各种书籍、画集、唱片、乐谱……木心逃课去选购,再将“战利品”雇车载回来。
回到学校,他开始在美专的图书馆里静静反刍:“这两间立满书柜阴森屋子,常由我一人独占,我亦只亮一盏灯,伦勃朗的亨德里克耶凭窗相望,柯罗的树梢如小提琴的运弓,塞尚的苹果一副王者相,基里柯的木筏欲沉不沉”。

青年木心(最左)
当时,他只知艺术使人柔情如水,后来浩劫临头,才知艺术也使人有金刚不坏之心。
木心的前半生,一直活在19世纪的异乡梦里。外面改天换地,他一心沉迷于文学和艺术:偷学意识流写作,与人彻夜谈论叶慈和艾略特,从14岁起写下的100多个短篇和8个中篇,集成厚厚的20本,直到1970年被抄没。
随后,浩劫来临。
1973年,木心因言获罪。关押他的,是一个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在这个地下室里,痛苦是一秒钟一秒钟进行的——“上一秒是痛苦,后来又是一阵痛苦”。
他有时候想,不如就这样死了吧,但另一个声音说,“我不甘心”。
在这样密不透风的黑暗里,木心恳求看守他的人:“给我纸笔,我要写交代材料。”
在拿到纸墨笔的那一刻,“我感觉许多人跟着我下去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他们陪着我下地狱了”。
在两年的监禁里,木心用写交代材料的纸笔,写了66页的狱中手稿,半张报纸大小的纸,密密麻麻,正反两面,每个字只有米粒那么大小,全部加起来约65万字。这些手稿的内容,可以追溯到木心童年时在茅盾书屋中读书的时光。在黑暗的地下室中,他开始与这些文学大师对话。
木心写:“我现在反而成了圣安东尼,地窖中终年修行,只要能拒绝内心的幻象的诱惑,就可清净一段时日,明知风波会再起,形役还将继续,未来的我,势必要追忆这段时日而称之为嘉年华。”
木心一生都没有控诉过这场牢狱之灾,提及时他只说——
“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

他把手稿叠成一小块一小块,塞在了棉衣棉裤的夹层里。“如果查到了,就是罪加一等,查不到,那些都是我的”。没有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结束,木心也从未想过,有一天这些手稿能够被人看到。
陈丹青说:“木心那个时代,很多人毁掉了,但是他说我不愿意毁掉。而这些手稿都是他不愿意被毁掉的证明。”
1975年,木心平反出狱。那批狱中手稿,他委托一位朋友保存。不久后,木心持着学生签证来到美国,那一年他已经56岁了。
1995年末,上海的一位朋友把手稿带到了纽约。时隔30年,这批在黑暗中秘密创作的手稿,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展出,这场展览,名字就叫“塔中之塔”。
“塔中之塔”——伦敦塔中的象牙塔。

即使身在囹圄之中,仍拥有一个更高、更美好、永远无法被摧毁的世界。
我们时常听人说,文学没有用。但是木心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学的用处不在于多赚几个钱,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过得更自在。人活在世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庸常中,但任何一个人,总会有一些需要超越庸常的时刻。
而文学所能做的,便是让一些伟大的灵魂陪伴你度过那些或高光、或至暗的时刻,帮助你以更好的方式,在面临重要的选择时,保有尊严、热爱和坚守。
所以,我们想给你推荐一门文学课。在知识付费市场,文学课程很少见,这也可以理解——我们得承认,大部分时候,文学的确没有什么世俗意义上的用处。
但如果你觉得生活不止眼前,还想拥有一个更宏大的世界,想要获得文学中那些优美而高贵的灵魂的守护。我向你郑重推荐这门课:
这门课程史无前例地聚集了10位顶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活着》作者余华,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苏童、张炜,金马奖最佳编剧严歌苓,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半个文坛集体出山,为你讲述他们的作品和人生,使这门课在推出之初,就轰动一时。
此外,这门课还聚集了12位一流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曹禺专家陈思和、鲁迅专家郜元宝、沈从文专家张新颖、科幻文学专家严锋……他们多是复旦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的主讲教授,共同构成这部课程的核心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