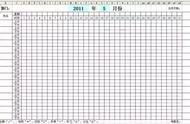“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在那里驻扎上一年,以24节气为结构,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叫《乡村里的中国》。” 2012年1月2日,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给著名摄影师焦波布置了一个“命题作文”,希望他深入农村,记录乡亲们的故事。经过半个月的踩点考察,焦波最终选取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作为拍摄地点。杓峪村一共167户人家,焦波和他的团队在2012年2月4日这天成为了村子里的第168户——“村儿电影社”。373天的拍摄、近1000小时的素材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焦波一行人朴实地到来、真诚地融入,用质朴而典型的故事描绘了真实的农民生存状态。影片表现了关心农民、关注农村、致敬农民的乡愁主题,被《党建》杂志评为“一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纪录片”。
98分钟的影片以二十四节气为纵轴,以三条平行交叉的故事线为横轴,在导演零介入、无偏见的前提下,采用直接电影的记录手法把在杓峪村发生的真实而全面的故事呈现给观众。它用真挚、素朴、勇敢而温暖的镜头告诉观众中国的农村既不是人们口中的脏、乱、差,也不是人们幻想的田园。这里有追求精神文化的农民杜深忠,有为村子忙前忙后却不被理解的*张自恩,有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杜滨才,还有家长里短、邻里纷争、婚丧嫁娶的酸甜苦辣事儿。《乡村里的中国》用细节和故事钩沉着时代遭遇的文明冲突,它既是中国农村生活的标本,也是一部追求永恒的纪录片范本。
本文将聚焦影片中的人物生存、情感关注以及生命本原,在体悟导演寓含其中的人文关怀基础上对农村的发展现状和农民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探析,从平淡的生活片段中分析存在于农村社会里深刻的公共议题及其现实意义。
一、人物生存
1.杜深忠: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
影片中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杜深忠,高中毕业,当过兵,担任过村支书,是杓峪村的“高材生”和“文化人”。写毛笔字、看新闻联播、拉二胡、搞文学创作,杜深忠的亮相打破了观众对于传统农民的认知,他对精神文明有着强烈的追求,四十年间从未断过。他宛如一个文艺青年,拥有梦想,不言放弃,但无奈的现实终究把它和土地捆绑在了一起,让他无法脱离。
对于这个“异想天开”的农民,土地的回馈是吝啬的。杜深忠一家辛辛苦苦栽种的苹果只收获了七千三百斤,以两块三毛五的价格出售,只挣了七八千块钱。砍倒玉米秸秆,掰下玉米棒子,夫妻两人忙活半年却也只有几袋玉米的收成。土地给予他的物质让他在无奈中维持着温饱,但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他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依然用他所热爱的文学、音乐和笔墨充盈着生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坐在马扎上一脸郑重地说:“我觉得人的素质上不去,物质反而成了负担,物质和精神要对应起来。”他花690块钱去买了心心念念的琵琶,期间虽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但他却乐观地说:“琵琶上弹出个好曲来,家庭也能弹出个好曲来,锅碗瓢盆交响曲。”
杜深忠和妻子的拌嘴日常浓缩了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在农村社会里的碰撞和冲突,把“精神文明何以求得保障”的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杜深忠对于文化的追求是他坚信“精神也需要滋养”的结果,而妻子却说他“头顶火炭不嫌热”;杜深忠对破坏生态者的深恶痛疾,在妻子眼里成了“穷得吱吱”;杜深忠挣钱少,妻子慨叹说:“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胚。”夫妻二人的言语冲突总离不开关于精神和物质的讨论,这看似常态化的争论背后其实是文化价值观念和物质利益观念矛盾的不断激化。
杜深忠的妻子代表了传统而务实的农民群体,他们关注家里的吃穿用度,“如何生存”的问题把操劳的内心占据得满满当当。他们崇敬知识分子,但否定农民和精神文明的联系。于他们而言,精神文化和精神文明成了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奢侈到农村的土地不该容纳一丝一毫。而富有情怀的杜深忠是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关注文化对每一代人的滋养。他们重新思考自己与土地的关系,“土地能给予农民什么?一年几千块钱收入,说实在的,对得起他们么?” 杜深忠身在农村,可他心里懂的东西却不局限于杓峪村这方天地。对于一个有理想却无门路的农民杜深忠来说,农村和土地埋葬了他的情趣和情怀,给他留下的只有无奈、失望和窘迫。他直言:“其实我一开始就对土地没有感情。”微薄的收入、贫窘的家境让这位才人面对现实发出了感叹,而这或许是他对待梦想最后的倔强。
2.张自恩:干一年支部*,赚了一肚子酒来。
影片中那个最忙碌的身影就是张自恩,他当过四年后勤兵,2002年开始担任杓峪村的村支书。村子里的大小事务都要张自恩来管理,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认真负责地处理村民矛盾、规划村庄建设、谋求村庄发展。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为杓峪村的发展尽心尽力的基层干部也会因为农村治理生态的复杂得不到理解,反被村民怀疑贪污要求上访查账。
张自恩是扎根土地的村官代表,身上有着农民的朴实和憨厚,也有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劲儿。杓峪村对他来讲不光是村庄,更是故乡。在这里处理村中事务既要考虑规则制度,也得考虑人情世故。生气、委屈、苦恼和无奈他统统咽进自己的肚子里,嘴上发着“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的牢*,实际上依然全心全力地为村民办事。
因修建小广场需要砍树,张光地和张自恩起了冲突,张自恩被指着鼻子骂。之后,张光地以村里账目有问题为由三番五次地上访查账,搞得张自恩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在不胜其烦的情况下对张光地破口大骂。村民张光爱和张光学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在邻里关系和孩子求学的问题上,张自恩不断地做两家的工作,寻求最优的和解方式。为了推进杓峪村的脱贫工作,张自恩四处奔走,他不断地到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会,向老板介绍村里的情况,过年过节也不忘提上东西去找老板拜年问好,以求项目能够稳步推进。
影片中有一幕,张自恩端着酒杯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他说道:“干一年支部*,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酒杯举在手里,却迟迟没有送到嘴边。或许张自恩不是最优秀的村干部,但他一定是最真实的村干部。他热忱的工作态度代表了千万基层干部的助农热心,他所面临的困境也代表了千万村官的尴尬处境。
二、情感关注
1.“家”的涵义重构在自省与理解之间
影片横向展开的情感线是杜滨才的故事。这个四岁时父亲患上精神病,母亲远嫁的单亲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少年,对于家的情感是复杂的。母爱的缺失和父爱的缺位让他从小经历着家庭破碎的痛苦和压力,家,成了他记忆中最遗憾也最难过的回忆。影片中,杜滨才不止一次地表达着对家的厌恶和反感,“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一回家就心烦,烦死了。”每次杜滨才在抱怨的时候,父亲杜洪法总是一言不发,默默地为儿子准备饭菜。
杜滨才对母爱的渴望和与母亲相见的胆怯是萦绕在他心头的一对矛盾,也是他纠结了十九年的原因所在。在渴望被关爱而又不知如何面对的杜滨才心里,母爱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婶子多次询问他要不要去见见母亲,她知道她住在哪儿。杜滨才每次都用“以后再说”来掩盖内心的情感。这个十九年的缺失和空白最终在相遇的那一刻被泪水冲垮了防线,儿子躲在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这是他盼了十九年的画面,是泪水决堤之下母亲形象的再出现、少年心结的终解开。
父爱的缺位、父亲的疾病和对一些情况的不满是杜滨才不愿回家的直接原因。他在家里极少与父亲交流,父子俩都是各做各的事。有一次,父亲发病拿着棍子要打人,被拉回家后,杜滨才严厉地“教训”父亲再怎么样也不能拿着棍子去打人。恢复过来的杜洪法像个犯了错的小孩,一边反思,一边又恳请儿子“别说了”以掩盖自己的尴尬。站在父亲面前,杜滨才说过一些叛逆的话,表达过一些负面的情绪,但他始终牵挂着这个家。作为父亲的杜洪法,他会在苹果收获的季节给儿子选一箱最好的留下,也会在苹果卖出去后给儿子汇报成果,告诉儿子没钱了跟他说一声。父子二人用各自的方式爱着对方,小心地、默默地,儿子给父亲争气,父亲让儿子放心。在杓峪村的春节联欢会上,杜滨才用一首《父亲》唱出了心底的爱与理解,在父亲转身、抹泪的一举一动中,爱的版图被重新拼凑,杜滨才也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
2.留守的儿童留守的心
影片中最令人痛心的画面是张自军的丧事,在贵州务工的他从八米高的脚架上跌落不幸身亡,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在面对父亲的棺材时,头扎孝带的儿子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张自军的父亲回答:“对了,那是你爸爸的家。”儿子追问:“怎么门口那么小?”对于这个孩子而言,他不懂得死亡的含义,更不明白天人两隔的意义。父亲常年的外出务工甚至让他模糊了父亲的形象、淡化了亲情的联系,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一种情感的缺失。
造成这种留守儿童被留守的直接原因就是经济条件的落后。家庭的困窘迫使父辈外出务工,距离的遥远阻隔着心灵的沟通,亲情缺失、陪伴缺失、亲子教育缺失……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正处于身心发育阶段的孩子找不到依靠,他们敏感、脆弱、内向、胆怯,对安全感有强烈的渴求,内心里向往完整和睦的家庭结构。他们习惯于向内诉说,遇到外人的时候格外羞怯。他们像被偷了翅膀的天使,总是小心翼翼地感知世界。
留守儿童的存在是农村的一个痛处,同时折射着外出打工农民无法选择的无奈。就像杜深忠在影片中说的,“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被逼出去的。”他们在经历“人肉换猪肉”的冒险,他们也不想自己的孩子被留守,可他们别无选择。导演焦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乡村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少些“人肉换猪肉”的悲剧。这何尝不是每一个来自农村个体的心声啊!
三、生命本原
生命的意义是一个解构人类存在的目的与意义的哲学问题。在民间,农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感知蕴含在丰富多彩的民俗和至高无上的信仰之中。农民对生命的思考表现为“天、地、人、神”的关系思考,就如《乡村里的中国》中所展示的那般准确、自然。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里万物复苏、生机孕育,春天是生命的起点。生就蕴涵着希望,生就代表着活力。所以,在立春这一天,杓峪村的村民们咬春(吃萝卜)、贴春字、缝春鸡,用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春天里祈愿,把美好的祝福送到杓峪村的每一个角落。
杜深忠在羊圈的墙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春字,并说“龙年春到发羊财”。羊,谐音“洋”,发洋财的意思就是发大财。缝春鸡的几位妇女互相调侃着“黄尾巴不好看”“红公鸡配绿尾巴”,有时说到缝制时的讲究,便脱口而出“头上缝个豆子,小孩不生痘子。”立春这一天,村子里还会举行篝火晚会,小孩子围着火把传递萝卜咬春,“谁咬着了谁就有一年的好时运”。一个小女孩咬到了萝卜后大喊:“我咬到春了,我咬到春了。”这时,一位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好不容易咬着春了,你还把它吐了。”现场顿时一片欢乐。祥和、朴素、轻松、欢愉的立春民俗是村民对一年崭新的期望,祈愿化作农民心中有力的精神支撑,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寻求神的庇护是农村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红白喜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张自军下葬时,帮忙的人喊道“孝子填仓,万石余粮”“满了吗”“满了”。在杓峪村,人死后便化作神,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保佑后代富足,好让悲伤的家属在情绪上得到安慰。而在杜海萍的婚礼上,女儿出嫁时需要烧香祷告,唱词为“观音奶奶两对包袱,月老两对,路神一对,保佑平安的一对”“今日良辰,三炷清香,酒席香案,请神高高在上,案前红绿包袱各一对,内有金银财宝,黄钱数尊,明人指点,凡人操办,今日吉时,以纸马香锞,隆重奉还,各路尊神永保佑善信女大喜之际,大吉大利,平平安安。”包括男方在迎娶新娘时也会说:“我把新娘的盖头挑一挑,想要两个大胖小。”
对神灵进行祈求是农民们寄托信仰的方式之一,他们通过神灵保佑和内心暗示获得吉祥福昭,祈祷中充满“向善”的内涵。他们用民俗信仰的力量诠释着生生不息,表达着质朴的生命思考。
四、总结
《乡村里的中国》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农村,展现了一群真实的农民。它把纪录片的纪实性和真实性充分发挥,把平淡日子的矛盾细节化呈现,做到了纪实客观与立意深刻的双重结合。这些每天发生在农村里的故事被总导演焦波准确捕捉,他把黝黑皮肤下的坚持、信念、热情、执著淋漓尽致地呈现,亦把关注农村发展的议题不断传播。关注底层人民体现了这部纪录片真正的价值。
指导老师:王华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