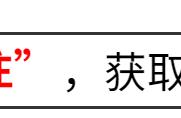即将到来的2020年2月2日,因其是极为罕见的对称日,但又因为这一天是周末,于是诸位有情人纷纷向当地“民政局”求情,借“难得一遇的爱你对称日”向外界狂撒一波来自2020的热气腾腾的狗粮,但谁曾想过,在古代,“情”却一直处于一种被禁锢的状态,而蒲松龄所创作的《聊斋志异》即向我们揭示了这个意蕴深远、永恒而亘古的爱情诉求。

蒲松龄
一、缘起缘灭几时休出身于书香世家的蒲松龄,在家中排行老四。在儒家思想浸透满朝的时代,一阵属于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之风又呼啸而来。当新的观念与传统的儒家相互碰撞,其思想也在蒲松龄的脑中有了些蛛丝马迹,而其所创作的《聊斋志异》正是当时的产物。
人、鬼、神、妖,诸方妖魔鬼怪来袭,且看蒲松龄如何巧运笔锋,斗转乾坤。
明末时期,蒲松龄降世,其主要生活是在清朝。晚明的思想文化被清朝打了个片甲不留,但思想因其传承与源流相继的特点,所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思维与观念一时间不可全然断绝,关于情感,自古多番论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视角下,先秦时期,魏晋时期和晚明时期是情感论内涵变化的突出节点。这里我们重点来谈谈明中叶时期的“主情说”。
先秦“言志说”开启了情感论的大门,提出“诗以言志”的看法,但这里需注意,此时的“志”却不是情感,而是个人的志向及抱负。魏晋时期“缘情说”成了古代有关情感论的第二大宣泄口,被誉为“太康之英”的西晋诗坛的代表之一——陆机曾道明:“诗缘情而绮靡。”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魏晋名门“颍川钟氏”之后钟嵘在其《诗品序》中说道:“诗乃‘吟咏情性’。”现在重头戏登场,泰州学派一代宗师李贽亮相,“主情说”便是因李贽的文学批评而初始显露。

李贽人物形象
二、花开花落又何妨当“主情说”怒起争锋之时,属于人的本性即被自然唤醒。所谓凡夫俗子防身利器之七情六欲,皆被晚明时期的批评家们看作是出自人的“真心”和“本性”的真实情感。
既然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又何错之有?
束缚人性的网被撕破了口子,爱情立马当先,于是乎,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纷纷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这样的社会背景也正是蒲松龄所生活的真实图景。
“火力全开”的理学在清代被宣传的扬扬沸沸,可理学的真面目却被一步一步地揭开。
“情之志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聊斋志异·香玉》

《聊斋志异·香玉》书籍
爱情的悲歌中呈现的是浪漫主义的至情意识,爱情的主旋律在欢唱着,是情感的盛宴也是时代的思潮。
那崂山太清宫下的一颗白牡丹,颇具盛名,蒲松龄因牡丹构思成文,书生与白牡丹的故事感动众人的同时,也是情感的另一番写意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