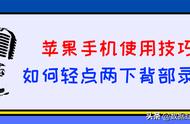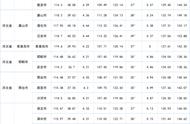位于苏格兰国家肖像画廊中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群像。
1752年,休谟在爱丁堡律师公会图书馆获得了一个职位,尽管薪水不多,却坐拥几千册图书,这就让他能够利用图书馆资源撰写英国史。哈里斯勾勒了一段休谟之前各种充满派系特征“英格兰史”的历史,这种状况激起了休谟写一部“不偏不倚的”、“公正的”历史的雄心壮志。他起笔于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到“光荣革命”的17世纪史分为两卷,随后追溯都铎王朝,写成两卷。休谟在这四卷历史中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品鉴大胆而犀利,尤其是对查理一世和劳德主教洒一把“同情之泪”、对伊丽莎白专制的嘲讽既不能让辉格派满意,又让托利派憎恨。
哈里斯认为,休谟不希望他的读者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相反,他希望以自己的修辞引导读者与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同情共感,同时,他还希望读者感受到他的历史著作与前辈历史学家争论的形式:那就是以托利派观点反对当时正统的辉格派。这一点在休谟的古代至中世纪历史中尤为明显。休谟认为英格兰的自由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古老宪政无关,1215年《大宪章》的条款并没有太大的“革命性”,“王室权力没有受到人民自由的制衡”,而是遭到“很多小专制者军事权力的遏制,这些人不仅威胁国王,同样也压迫臣民”。休谟的评论与当时的辉格正统派完全相悖。而他对玫瑰战争的描述力图让读者感受到新朝建立的基础并不源于人民的同意,而是靠征服和篡夺。某种程度上,休谟在其历史著作中践行哲学的精神,也展现了他过去对政治、经济、社会发表的那些观点。
在《大卫·休谟思想传》这部思想传记中,哈里斯简短叙述了休谟与法国文人的交往,比较了休谟与卢梭政治哲学上的分歧,而约翰·威尔克斯引发的事件促使休谟“回应”那个时代的政治状况,“自由与权威”应该如何平衡?休谟晚年挂念最多的恐怕是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然而,这本在休谟去世后出版的著作却没有“激起这个世界的喧嚣”。这大概是休谟及其友人预料之外的。休谟一生的著作是否如《我的一生》中所说的那样“无人问津”、“大为光火”之类?哈里斯认为事实并非如休谟所言,“即便他没有信徒,也没有鼓吹什么流派,他去世时仍然是那个时代最著名、最广受尊敬的文人之一”。实际上,《我的一生》隐藏的作为一个文人获得“财务自由”的细节,也揭示出休谟被其同时代人接受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足以证明他在其自传中所说的“年轻时的文学梦想”“全部实现”了。

《休谟的日常生活哲学》,作者: [美]唐纳德·利文斯顿,译者: 李伟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哈里斯在这部思想传记中结合17、18世纪欧洲的思想争论解析了休谟著作中的观点,仿佛拉近了读者与休谟的距离,让读者感受到休谟与同时代文人的对话与辩论。不过,这幅休谟思想肖像有多真切呢?在回应学者们对其思想传记的批评时,哈里斯将休谟比喻为“一只狐狸,而非刺猬”,其“躁动不安的心灵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从哲学到文学,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宗教,不断的探索造就了休谟的文学成就。这种理解将休谟的每部著作视为独立的表达,这就启发读者和研究者们重新理解休谟的创作和思想。
休谟之哲思距今二百余年,却似未曾远离当下世界。他那些散发真知灼见的散文仍然提醒这个世界:猜忌——不仅仅是贸易猜忌,仍然横行于各国之间,导致国家之间或冷或热的冲突。迷信与狂热,仍然会在人群中蔓延,导致盲从和动荡。他对英格兰自由的历史叙述、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品鉴让读者警惕那些流行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可接受或批驳。他将正义之德视为激情和习惯的产物而非理性的设计,将政府的起源归因于人们的意见,这些主张仍然会激起今天读者对道德和政治的反思。于今日之读者,休谟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抑或政治经济学家等,每一个面相都意味着一种单独的言说者。当所有面相综合起来时,那种单独的熟悉的形象忽然又变得模糊而遥远了。或许休谟和莎士比亚一样,也是“说不尽的”。
撰文/张正萍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