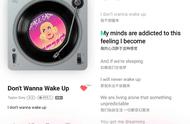如所周知,图像很早即被视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学者所重视。如唐人张彦远即强调图像传达“既往之踪”具有文字不可比拟之优势[1];南宋人郑樵创制《图谱略》,也提倡图像与文字互相印证,是为另一种形式的“左图右书”[2]。而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学界,图像也受到历史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史家逐渐意识到图像作为资料在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由此图像被视作历史文献,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及至20世纪,以图证史更是成为历史学者探求过去的重要法门[3],而“图像证史”等概念的提出无疑正是此研究取径的集中体现[4]。
不过另一方面,图像与历史能否联系及如何联系,也引发一些研究者的警惕。如曾宣称历史研究应以图像为先的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在其晚年即反省过分强调视觉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会导致历史科学的毁灭[5],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1928-2000)也提示历史与艺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必然差异,不能等同处理[6]。而在进入21世纪后,曹意强[7]、缪哲[8]、邓菲[9]、陈琳[10]、黄厚明[11]、张长虹[12]、孟彦弘[13]等中国学者也先后对以图证史或以史证图的研究取径提出反思:他们充分认识到“图像证史”的陷阱,指出图像具有多义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图像生成过程极不确定,甚至不乏造伪,且图像意义随时间而流动,而图像固有的保守与历史现实间也往往存在龃龉。基于这样的反思,他们强调图像作为资料的主体性,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反对将图像仅仅作为文字的“佐证”,成为历史研究的“插图”或“陪衬”。这样的反思也影响到具体研究层面,如当前艺术史研究对图像程式、格套粉本的关注,某种意义上或正是对此的回应。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再来看传世名画《历代帝王图》中一个显而易见却迄今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即图中帝王身着不同冠服:十三位帝王中,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著冕服,而汉昭帝刘弗陵、陈宣帝陈顼、陈文帝陈茜、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却与此有异。画家在绘制历代帝王肖像时为何要选择不同冠服?其以冕服加于光武、魏文等七帝,依据是什么?与之相对,汉昭、隋炀及陈朝四帝为何又被配以其他冠服?画家如此设计,是“别有用心”还是另有所据?无待赘言,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澄清《历代帝王图》的创作过程,对于理解图像与历史的联系亦可提供启示。以下我们即以《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冠服的差异为线索,从动态视角观察这种差异的形成,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图像证史”提出一点反思。
一、《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发现与解读
无待赘言,《历代帝王图》中诸帝王冠服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眼即可看出,然而吊诡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代帝王图》这一独特“表现”在相关著录、题跋中均未有所呈现[14],直到元人王恽才首次将之明确标示出来,云:
阎立本画古帝王一十四人:汉文昭帝、光武皇帝、魏文帝丕、蜀昭烈皇帝、吴孙权、晋武帝炎、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后主叔宝、陈文帝、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炀帝。……十四帝除汉文、陈宣、废帝、后主、炀帝,余皆衮冕,若五方帝之仪。[15]
显然,王恽注意到汉文帝(应为汉昭帝)、陈宣帝等(漏陈文帝)所著冠服与其余诸帝有别,后者“皆衮冕,若五方帝之仪”。不过,王恽称著衮冕的帝王形象如五方帝,似不尽准确。严格说来,彼时五方帝的形象大约有着衮冕和着通天冠两种。前者如河北石家庄毗卢寺毗卢殿(图1a)、怀安昭化寺大雄宝殿、山西繁峙公主寺大佛殿、浑源永安寺传法正宗殿、阳高云林寺大雄宝殿绘明代水陆画及山西右玉宝宁寺明代水陆画、明刻版画《水陆道场神鬼图像》等,图中多题作“五方五帝”的五方帝皆着衮冕;后者如山西稷山青龙寺腰殿绘元代水陆画(图1b)、河北蔚县故城寺大雄宝殿绘明代水陆画等,五方帝则着通天冠。

图1a 毗卢寺明代水陆画之五方帝采自《毗卢寺壁画》,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图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