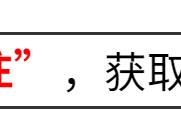我聆听,却不知道
我听到的是寂静
抑或上帝。
[……]
索菲娅·安德雷森
第一次见到女人时,我十一岁。这件事突如其来,我毫无准备,震惊得哭了起来。在我生活的荒野里,只住了五个男人。我爸爸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简单地叫作“耶稣撒冷”。这里是耶稣逃离十字架的地方。就这样,没了。
我家老头——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1]——向我们解释说,世界毁灭了,而我们是最后的幸存者。在地平线之外,只剩下没有生命的土地,被他笼统地称为“那边”。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如此总结了整个星球:荒无人烟,没有道路也没有动物的踪迹。在那些遥远的地点,甚至连长有羽毛的游魂都已经灭绝。
然而,在耶稣撒冷却只有活物。这里的人不知何为怀想,何为希望,但却是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我们存在得如此孤独,甚至不曾染上疾病,而我一直相信我们是不死的。在我们周围,只有动物和植物会死去。干旱时节,我们那条无名的河会假装昏厥,它是一条小河,从我们营地的后方穿过。
人类有我,我爸爸,我哥哥恩东济,还有我们的仆人扎卡里亚·卡拉什——你们接下来会发现,他没什么存在感。此外就没有别人了。或者几乎没有。说实话,我忘记了两个“半居民”:母骡泽斯贝拉,她极富人性,甚至能满足我老爸的性幻想。我也没说起我舅舅阿普罗希玛多[2]。这个亲戚值得一提,因为他并不与我们一同住在营地里。他住在围栏入口的地方,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距离,只会时不时地来拜访我们。在我们与他的小茅屋之间,隔着野兽与几小时的路程。
对我们这些小家伙来说,阿普罗希玛多的到来是盛大欢庆的理由,是我们贫瘠单调生活中的微小振动。舅舅会带来食物、衣服等必需物资。我爸爸紧张兮兮地出门,去迎接堆满包裹的卡车。在卡车侵入围绕房子的栅栏之前,他便拦下来访者。在栅栏那儿,阿普罗希玛多被迫先洗澡,以免把城里的传染病带进来。哪怕天气寒冷、夜幕降临,他也要用土和水将自己清洗干净。洗完之后,希尔维斯特勒从卡车上卸货,尽量加快交货速度,减少告别时间。在飞逝的瞬间,甚至比翅膀扑扇的时间还短,阿普罗希玛多便在我们焦灼的目光中返程了,消失在地平线之外。
“他不是我嫡亲的兄弟,”希尔维斯特勒辩解道,“我不想跟他说太多,这个男人不了解我们的习惯。”
这个小小的人类团体就像五根手指一样团结在一起,但还是有所区分:我爸爸、舅舅和扎卡里亚有着深色的皮肤;我和恩东济同样是黑人,但肤色更浅。
“我们是另一个种族吗?”某一天我问道。
“没有人是某一种族的。种族,”他说,“是我们穿在身上的制服。”
希尔维斯特勒或许有道理。但我却在很晚之后学到,有时候,这件制服会粘在人的灵魂上。
“这种浅色皮肤来自你的妈妈,朵尔达尔玛[3]。小达尔玛有一点点混血。”舅舅解释说。
家庭、学校、他人,所有这些都在我们心中燃起一点可期许的火花,开辟一块可供我们闪耀的领地。一些人为唱歌而生,另一些为跳舞而生,其他一些人仅仅为了成为其他人而生。我为保持沉默而生。我唯一的志向就是寂静。向我说明这点的是我的爸爸:我具有不说话的倾向,具有提炼许多寂静的天赋。我写得没错,许多寂静,是复数。对,因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寂静。而所有寂静都是妊娠阶段的音乐。
当有人看到我一动不动地躲在隐蔽的角落,我不会受到惊吓。我正忙着,身心都被占据:我在纺织用以制作宁静的细线。我是调试寂静的人。
“过来,我的孩子,过来帮助我保持沉默。”
傍晚时分,老头靠在阳台的椅子上。每晚都是这样:我坐在他的脚边,望着高空黑夜中的星星。我爸爸闭上眼睛,摇头晃脑,仿佛有一枚罗盘指引着那种沉静。随后,他深吸一口气说:
“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美的寂静。谢谢你,姆万尼托。”
适宜地保持沉默需要多年的练习。而对我来说,这是种天赋,是某位先人留下的遗产。也许是遗传自我的妈妈朵尔达尔玛,谁说得准呢?由于太过沉默寡言,她不再继续存在下去,却没人发现她已不在我们这群存活的生物之间。
“你知道的,儿子:有一种属于坟墓的平静。但这个阳台上的宁静是不一...
我爸爸。他的声音如此难以察觉,就像是另一种类别的寂静。他咳嗽,他的咳嗽声嘶哑,这是一种隐秘的言语,没有词汇也没有语法。
在远处,附屋的窗户上,能够隐约看到一盏闪烁的灯。我的哥哥一定在窥视着我们。一股负罪感涌上我的胸口:我是天选之人,唯有我能亲近我们永恒的爸爸。
“不把恩东济叫过来吗?”
“别管你的兄弟了。我更喜欢独自与你待在一起。”
“但我已经有些困了,爸爸。”
“再留一小会儿。是愤怒,太多积攒下来的愤怒。我需要消除这些怒火,我的心里已经装不下它们了。”
“是什么愤怒,我的爸爸?”
“多年以来,我饲养野兽,却以为自己养的是宠物。”
说有困意的是我,但睡着的却是他。我留他在椅子上打瞌睡,自己回到了卧室。而恩东济仍然醒着,等待着我。我的哥哥看着我,眼中混杂着妒忌与怜悯:
“又是这种寂静的把戏吗?”
“别这么说,恩东济。”
“这个老家伙疯了。更糟糕的是那家伙根本不喜欢我。”
“他喜欢的。”
“那他为什么从来不叫我过去?”
“他说我是调试寂静的人。”
“所以你就信了?你没发现这是个巨大的谎言吗?”
“我不知道,哥哥,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他就喜欢我在那儿待着,一句话也不说。”
“你难道没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交谈吗?事实是你让他想起了我们去世的妈妈。”
恩东济无数次地提醒我,为什么爸爸将我选为他最偏爱的孩子。这种偏爱的原因出现在一个瞬间:在妈妈的葬礼上,希尔维斯特勒还不知道如何面对鳏居的境况,躲在角落里涕泗横流。正在那时我靠近了我的爸爸,为了迎接我三岁的小小身躯,他跪了下来。我抬起双臂,却并未擦拭他的脸庞,而是将两只小手放在他的耳朵上,似乎想将他变成一座岛屿,隔绝世上一切的声音。在这个没有回声的区域里,希尔维斯特勒闭上眼睛:他看到朵尔达尔玛并没有死。他的胳膊盲目地在半明半暗中伸出:
“小达尔玛!”
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个名字,甚至不曾回忆起他作为丈夫的时光。他希望这所有的一切都缄默不语,在遗忘的坟茔中入土为安。
“而你要帮我,我的儿子。”
对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而言,我的志业已经确定:照看这份不可救药的缺失,管理那些吞噬了他睡眠的魔鬼。有一次,当我们共享寂静时,我鼓足勇气:
“恩东济说我令你想起妈妈。这是真的吗,爸爸?”
“正好相反。你使我远离那些记忆。恩东济却会让我想起那些曾经的痛苦。”
“爸爸,你知道吗?我昨晚梦到了妈妈。”
“你怎么能够梦到从未见过的人呢?”
“我见过,只是不记得了。”
“那是一回事。”
“但我记得她的声音。”
“她的什么声音?朵尔达尔玛几乎从来不说话。”
“我记得一种宁静,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是水。有时我觉得我记得家,记得家的伟大宁静。”
“那恩东济呢?”
“恩东济什么,爸爸?”
“他坚持说能想起你们的妈妈吗?”
“他没有一天不想起她。”
我爸爸没有作答。他反复咀嚼着嘟囔的线团,之后,他用到过灵魂深处的嘶哑嗓音说道:
“我要说一件事,而且决不会再重复:你们不能想起或梦到任何东西,我的孩子。”
“但我会做梦,爸爸。而恩东济能记得那么多事情。”
“那都是谎言。你们梦到的都是我在你们的头脑中创造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爸爸。”
“而你们记得的都是我在你们的头脑里点亮的。”
梦是同死者的交谈,是前往灵魂国度的旅程。但无论死者还是灵魂之地都已不复存在。世界完结了,其结局是一种绝对的终止:没有死者的死亡。死者的国家废除了,上帝的王国取消了。我爸爸就是这么说的。时至今日,在我看来,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的这番讲解显得阴森而又混乱。然而,在那个时刻,他却代表了最终论断:
“正因如此,你们既不能做梦,也不能回忆。因为我本人就不做梦,也不回忆。”
“但是爸爸,您就没有对于妈妈的记忆吗?”
“对于她,对于房子,对于一切,我都没有任何记忆。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接着,他站起来去热咖啡,脚步嘎吱作响。这些脚步就像将自己连根拔起的猴面包树。他看了看火,假装在照镜子,然后闭上眼睛,呼吸咖啡壶散发的芬芳蒸气。他依然闭着眼睛,轻声说:
“我要讲述一桩罪恶:你出生之后,我便不再祷告了。”
“别这么说,我的爸爸。”
“我现在就告诉你。”
有人生孩子是为了更加接近上帝。而他自成为我的爸爸之后,便将自己变成了上帝。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便是这样说的。他接着道:那些悲伤虚伪的人,那些孤独的坏人,相信他们的悲痛能够到达天上。
“但上帝是聋子。”他说。
他停顿了一下,拿起杯子品了口咖啡,接着把话说完:
“即便他不是聋子,又有什么话能对上帝说呢?”
耶稣撒冷并没有石制的教堂或者十字架。正是在我的沉默中,我爸爸建起了主教堂。正是在那里,他等待着上帝的回归。
* * *
事实上,我并非出生在耶稣撒冷。我是,这么说吧,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移民,那个地方没有名字、没有地理、没有历史。在我三岁那年,我妈妈刚刚去世,我爸爸便带着我和我哥哥离开了那座城市。在穿越了森林、河流与沙漠之后,他到达了一个在他看来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在这场艰苦的跋涉之中,我们与无数反方向行进的人擦身而过:他们从乡村逃向城市,从乡村的战争中逃离,在城市的悲惨中寻求庇护。人们都很好奇: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家庭要躲进水深火热的内陆地区?
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我爸爸向前行进。他看起来有点感到恶心,也许他本以为这趟行程应该更多的在船上,而不是在公路上。
“这是机械化的诺亚方舟。”他如此宣告,彼时我们还坐在那辆旧汽车上。
与我们一起坐在汽车后排的,还有扎卡里亚·卡拉什,这位曾经的军人会在日常事务上帮助我的父亲。
“但我们要去哪里?”我哥哥问。
“从这一刻起,‘哪里’便不存在了。”希尔维斯特勒断言道。
在漫长旅途的终点,我们在一片围栏中早已荒芜的土地上安顿下来,栖身于猎人遗弃的营地里。四周,战争将一切夷为平地,毫无人类的踪迹,甚至连动物都很罕见。充裕的只有野生丛林,而那里已经很久没有开辟过一条道路了。
在营地的瓦砾上,我们安顿下来。我爸爸,中心的废墟;我和恩东济,住在附屋;扎卡里亚自行安置在一间旧储藏室,位于营地的后方。原先办公用的房间依旧空着。
“那间房子,”我爸爸说,“由幽灵居住,由回忆管理。”
之后,他下令:
“那里谁也不许进入!”
修复的工作极少。希尔维斯特勒不想破坏那些被他称为“时间的作品”的东西。他仅仅做了一件事情:在营地的入口处有一个小广场,那里的旗杆上曾悬挂着各种旗帜。我爸爸将旗杆变成了支架,用以放置一个巨大的耶稣受难像。在耶稣的头顶,他固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欢迎,圣主上帝。”这是他的信仰:
“有一天,上帝会来向我们请求原谅。”
舅舅和帮手在胸前慌乱地划着十字,咒骂这种异端思想。我们露出信心十足的微笑:我们将享有某种神圣的庇护,让我们永远不会受到疾病之苦,不会被蛇咬到,或者遭遇野兽的伏击。
* * *
我们无数次地发问: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远离一切,远离所有人?我爸爸回答说:
“世界终结了,我的儿子。只剩下耶稣撒冷了。”
我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但恩东济却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妄想。他不依不饶,继续发问:
“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了吗?”
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深吸一口气,仿佛这个答案要花费很多气力。接着,他将这口气缓缓吐出来,低声说:
“我们是最后的几个。”
维塔里希奥十分勤勉,他精心细致地照顾我们,为抚育我们而忙碌不已。但他却极力避免这种照顾演变为柔情。他是男人。而我们在成为男人的学堂里。最后仅存的几个男人。我想起,当我拥抱他时,他优雅却坚定地远离了我:
“你拥抱我时,闭上眼睛了吗?”
“我不知道,爸爸,我不知道。”
“你不应该这样。”
“不该闭上眼睛吗?”
“不该拥抱我。”
尽管保持着身体上的距离,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依然同时肩负起父母的职责,承担起现世祖先的角色。我对这种细致感到奇怪。因为这种热忱否认了他所宣扬的一切。除非在某个未知的地方仍有无尽的未来,这种付出才有意义。
“但是爸爸,你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消亡的呢?”
“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阿普罗希玛多舅舅……”
“舅舅讲了许多故事……”
“那么,爸爸,您也给我们讲讲吧……”
“事情是这样的:在世界末日之前,世界便终结了……”
宇宙无声无息地走向尽头,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它日渐败落,枯竭至绝望。就这样,我爸爸空洞地叙述了宇宙的湮灭。首先灭亡的是阴性的地点:河流源头、海滩、湖泊。之后,阳性的地点也消亡了:聚居地、道路、港口。
“只有这里幸存下来。我们会在这儿永远生活下去。”
生活?生活是实现梦想,期待消息。希尔维斯特勒既不做梦,也不等待消息。一开始,他想要一个没人记得他名字的地方。现在,连他本人也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阿普罗希玛多舅舅会给爸爸狂热的想法泼冷水。他说自己的妹夫离开城市的原因非常普通,在为年龄所困的人群中尤为常见。
“你们的爸爸抱怨说他觉得自己老了。”
衰老无关年龄,而是疲惫。当我们变老之后,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这便是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的抱怨。当他决定完成一次全面的旅行时,所有的居民与地点都已变得难以区分。另一些时候——这些时候非常多——希尔维斯特勒则会宣称:生命太过宝贵,不能在无趣的世界中浪费。
“你们的爸爸现在很像心理学家。”舅舅得出结论。“过些日子,这种情况会过去的。”
漫长的时光逝去,我爸爸却妄想依旧。随着时间流逝,舅舅出现得越来越少。我因为他越来越多的缺席而感到痛苦,而我哥哥则修正了我的想法:
“阿普罗希玛多舅舅并非你想象的那样。”他提醒我。
“我不明白。”
“他是个监狱看守。这就是他,一个监狱看守。”
“怎么会?”
“你的小舅舅正看管着这个关押我们的监狱。”
“那我们为什么要待在监狱里?”
“因为罪行。”
“什么罪行,恩东济?”
“我们爸爸犯下的罪行。”
“哥哥,别这么说。”
所有爸爸用来解释我们为何背离世界而编造的故事,所有那些离奇的版本都只有一个目的:遮蔽我们的理智,使我们远离过去的记忆。
“真相只有一个:我们家老头子正在逃脱制裁。”
“他犯了什么罪?”
“我之后再告诉你。”
* * *
无论逃离的原因是什么,八年前,指挥我们撤离的都是阿普罗希玛多。他开着一辆快要报废的卡车,将我们带到了耶稣撒冷。舅舅早先就知道这个为我们预留的地方。有一段时间,他在这个古老的营地工作,负责监管狩猎。舅舅了解野兽与猎枪、草丛与森林。他一边用破车载着我们,一只胳膊搭在车门上,一边讲述动物的狡诈与丛林的秘密。
这辆卡车——也就是新的诺亚方舟——到达了目的地,但也永远瘫痪下来,停在后来我们家园的入口处。它在那里腐化生锈,也在那里成为我最心爱的玩具,成为我梦想的庇护所。坐在损坏机器的方向盘前,我本可以战胜距离与围栏,创造出无尽的旅程。我本可以像其他任何孩子一样,环绕整个星球,直到全世界都臣服于我。然而这些从未发生:我的梦想并未学会旅行。一个钉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不懂得梦想其他地方。
幻觉消减之后,我开始寻求其他的方式来对抗忧伤。为了嘲弄缓慢流逝的光阴,我宣告:
“我要到河边去!”
也许没有人能听到我的话。然而,这声宣告却让我欣喜若狂,以至于我一边不断地重复它,一边向峡谷走去。在途中,我停在了一根死去的电线杆前,这根电线杆被树立起来,却从未投入使用。其他插在地上的电线杆都萌发出绿色的新枝,如今已经成为参天大树。唯有那根瘦骨嶙峋地死去,独自面对着无尽的时间。那根杆子,恩东济说,并非插入地下的树干,而是一根桅杆,属于一艘失去了海洋的船。因此,我常常拥抱它,借此获取来自年长亲人的安慰。
在河边,我徜徉在被驱散的梦里。我等待着我的哥哥,他傍晚时会过来洗澡。恩东济脱掉衣服,他就这样,保持着毫无庇护的状态,满怀忧伤地看着水面,正如他满怀忧伤地凝视着那个旅行箱——每一天,他都会将那个旅行箱装满,然后清空。有一次他问我:
“你在水下待过吗,小家伙?”
我摇了摇头,自知我并不明白他问题中的深意。
“在水下,”恩东济说,“能够看到无法想象的东西。”
我并未破解哥哥的话。然而,不久之后,我便感觉到:在耶稣撒冷,最真实、最有生机的便是那条没有名字的河流。毕竟,对泪水和祷告的禁令自有其意义。我爸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超脱世外。如果必须要祈祷或哭泣的话,一定会在那里,在河边,膝盖弯曲跪在潮湿的沙子上。
“爸爸总说世界灭亡了,不是吗?”恩东济问。
“爸爸说了那么多。”
“恰恰相反,姆万尼托。不是世界灭亡了。而是我们死了。”
我汗毛直立,一股寒意从灵魂蔓延到肌肉,从肌肉蔓延到皮肤。原来我们的住处就是死亡本身吗?
“别这么说,恩东济,我害怕。”
“那你就记着:我们不是离开了世界,而是被放逐了,就像从身体里拔出倒刺一样。”
他的话刺痛了我,仿佛生命正插在我的身体中,而为了成长,我必须将这根倒刺拔出来。
“将来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恩东济结束了谈话,“但是现在,我的小弟弟难道不想看看另一边吗?”
“什么另一边?”
“另一边,你知道的:就是世界,‘那边’!”
在回答之前,我朝四周窥视了一番。我害怕爸爸正监视着我们。我窥视了小山的顶端、房屋的后方。我害怕扎卡里亚从这里经过。
“把衣服脱了,去吧。”
“你不会害我吧,哥哥?”
我想起来,有一次,他将我扔在平静的泥水中,我被困在底部,双脚被水下的芦苇根茎缠绕。
“跟我来。”他邀请道。
恩东济将脚浸在泥里,走进河流。他走到水及胸深的地方,鼓动我到他身边。我感受身边转动的水流。恩东济将手伸向我,害怕我被水流冲走。
“我们要逃跑吗,哥哥?”我问道,带有一种克制的兴奋。
我为自己从未想到这点而感到难过:这条河流是一条开阔的道路,一道没有阻碍的宽敞垄沟。出口就在那里,而我们却未曾看到它。想要高声制订计划的*越来越强烈:也许我们可以回到岸边,开始制作一条独木舟?没错,一条小独木舟就足以让我们离开监狱,带我们驶向广阔的天地。我盯着恩东济,而他对我的幻想依旧无动于衷。
“不会有独木舟的,永远不会。忘掉它吧。”
我难道没有听过,在下游,这条河会遭受鳄鱼与河马的侵袭?还有急流和瀑布,总之,就是这条河隐藏着无尽的危险与陷阱?
“但是有人已经去过了吗?我们只是听说……”
“安静点,别说话。”
我随着他逆流而上,在波涛中破浪而行,一直到达河流的转弯处,我后悔了,此处的河床都布满了滚动的石子。在这片平静的水域,河水清澈得令人震惊。恩东济松开我的手,并指导我:我应当照他的样子做。于是他潜入水中,等整个人都没入水中时,睁开眼睛,凝视水面闪烁的光。我就是这样做的:在河流的肚腹内,注视太阳的光芒。这种光辉令我目眩,让我沉浸于一种甜蜜包裹的盲目之中。如果有母亲的拥抱,就应该是这样,令人的感官感到晕眩。
“喜欢吗?”
“我喜不喜欢?简直太美了,恩东济,它们就像流动的星辰,却亮如白昼!”
“看到了吗,小弟弟?这就是另一边。”
我再次潜入水中,让自己沉醉在这种美妙的感觉里。但这一次,我却突然感觉头昏,顷刻之间,我失去了对自己的意识,混淆了水底与水面。我像一条失明的鱼,在原地打转,不知道如何浮上水面。倘若不是恩东济将我拽上岸边,我一定会溺水而亡。恢复意识之后,我坦白说,在水下时,突然感觉到一阵战栗。
“在另一边,难道有人在窥视我们吗?”
“是的,有人在窥视我们。是那些将会来捞我们的人。”
“你说的是‘找’?”
“‘捞’。[4]”
我浑身发抖。这种变成鱼、被困在水里的想法令我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在太阳那边的其他人,是活物,也是唯一的人类生物。
“哥哥,我们真的死了吗?”
“只有活人才可能知道,弟弟。只有他们。”
河中的意外并未阻止我。相反,我继续回到河流转弯的地方,在平静的水域,放任自己沉没下去。我在水下待了很久很久,眼花目眩地拜访了世界的另一边。我爸爸从不知道,但正是在那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我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调试寂静的技艺。
[1] Silvestre Vitalício,意为“终身的野蛮人”。
[2] Aproximado,意为“靠近的人”。
[3] Dordalma,与“Dor da Alma”同音,意为“灵魂之痛”,后面的小达尔玛(Alminha)则意为“小灵魂”。
[4] 这里的“找”和“捞”是葡语中两个读音相近的词“Buscar”和“Pescar”,前者的意思是“寻找”,后者的意思是“钓鱼、捕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