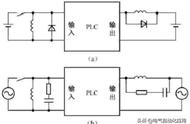斯巴达的国王阿吉斯四世(Agis IV)和克列欧美涅斯三世两个人的生平事迹都发生在斯巴达历史上的同一时期,即公元前3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把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与格拉古兄弟俩进行平行比较,只是一种勉强的做法,整个的来说是不太准确的。首先,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不是兄弟,尽管直到其中一个人死后,他们才算是发生了一点*克列欧美涅斯娶了阿吉斯的孀妇阿基阿蒂斯(Agiatis)作妻子。
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并不是斯巴达人民的正式代表,而格拉古兄弟俩则是经民众投票选举出来担任护民官的。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都是世袭的国王,分别在公元前244年至前241年和公元前235年至前222年继承了欧里庞提德和阿基亚德的王位。然而,普鲁塔克肯定不会是第一个看出,在这两个斯巴达国王与两个罗马护民官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之处。这两个斯巴达人同样都是在激烈的国内斗争中被*害的,而且两人都明确地支持一种激进的、即使不是革命性的社会改革方案,他们都曾经试图通过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实施这样的改革。

图|罗马养老院
那么,阿吉斯四世和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到底做了什么,以致连他们的性命都搭上了呢?显然,仅仅依靠普鲁塔克的《传记》,是不足以为如此复杂的问题找到可能的答案的。首先,我们必须调查普鲁塔克选择的那些历史文献的性质是什么,尤其是它们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有一个作家,即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历史学家菲拉尔克斯(Phylarchus),他与普鲁塔克所记载的一些希腊人物基本属于同一时代,也是普鲁塔克首选的资料来源。但是,菲拉尔克斯记述的内容又有多少值得信赖的呢?如果我们相信罗马崛起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阿卡狄亚人波利比奥斯(Polybius)对此人所作的猛烈批评的话,那么他根本就不值得相信。
菲拉尔克斯记述的材料,实际上是被波利比奥斯特意挑选出来作为优秀的历史写作的反面范例的。菲拉尔克斯让波利比奥斯感到难受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的文体风格,因为他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即把本应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编纂与虚构的、富于情感的悲剧混为一谈。但是,波利比奥斯本人也曾因为偏见而受到人们的指责。大约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他出生在“大都会”,属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这段时期里统治亚加亚联盟的贵族精英。

图|修昔底德雕像
就相关的历史写作而言,他曾明确地声称偏爱自己的祖国才是真正的爱国。斯巴达的克列欧美涅斯三世是一个性格坚毅的人,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亚加亚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敌人;在波利比奥斯的父辈们所处的时代里,“大都会”曾经确实遭受过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的洗劫和野蛮对待。这是波利比奥斯感到无法接受的事实,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去驳斥菲拉尔克斯对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的美化。真相究竟在哪里?很不幸,普鲁塔克选择遵从菲拉尔克斯对历史的阐释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菲拉尔克斯其实只是一个喜欢说教的传记作家,而不是一个最好的历史学家。
因此,我们最多只能宣称,我们的记述不会与菲拉尔克斯、波利比奥斯和普鲁塔克所记载的事实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同时,这些事实保持了原样,没有什么渲染;而且,我们对这些事实的阐释,最起码使斯巴达历史上一段最引人入胜、也最为重要的插曲获得了前后一致的意义。这段插曲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一个原因就是斯巴达妇女们的作用不但显得非常突出,而且在事实上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情形在整个希腊(或罗马)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亚里士多德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在他的《政治学》里说过:在斯巴达人统治的时候,很多事情是由妇女来完成的。这句话可能主要指的是从公元前44年到前371年这段时间。然而,在公元前244年与前221年这段时间中,这一相当受争议的言论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并得到了证实。我前面已经提及过,克列欧美涅斯娶了阿吉斯四世的孀妇-阿基阿蒂斯。此外,普鲁塔克告诉我们,阿基阿蒂斯曾千方百计地想要报*夫之仇,并且她比自己的丈夫还要更急于实行改革的方案,她的丈夫当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遭人谋害的;她还促使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克列欧美涅斯转变成了一位改革者。
在当时,阿吉斯的母亲和祖母-阿格西斯特拉塔(Agesistrata)和阿尔奇达米娅(Archidamia),她俩被普鲁塔克言之凿凿称为“所有斯巴达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当中最富有的人”,而且,她们都同样毫不含糊地支持阿吉斯的改革事业;最后但同样也绝对重要的是,克列欧美涅斯的令人敬畏的母亲-克拉提西克列娅(Cratesicleia),她在自己的儿子被流放之前就曾到托勒密三世的宫廷当人质,并且,她在那儿也是因为一场血腥的派系斗争而遭到*害的。在希腊语中,表示内乱、派系斗争或内战的词是“stasis”(在现代希腊语中表示“巴士站”)。

图|斯巴达遗址
因为“stasis”有时会威胁到一个希腊城邦(polis)的生存,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的第五卷的主题就是如何预防和避免出现“stasis”。但是,从事实上看,这样显然也收不到多大的效果,或者说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和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没有什么两样,仍然继续受到“stasis”的折磨。不过,公元14年这段时间在表面上有点新意的地方是斯巴达也开始出现了“stasis”;这个城邦在先前的年代里向来是以有序、有效地治理(eunomia)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而闻名于天下的,可现在它也与其他希腊城邦一样被“stasis”搅得焦头烂额。
而且,在斯巴达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在土地财产的分配和拥有上出现了极端而且持续恶化的不平等现象。在以前,让斯巴达人感到自豪的正是与之相反的状况。他们所夸耀的“平等者”(Similars)之间的政治平等,是以在公民之间实现了一种根本性的经济平等为基础的;这种经济平等应该追溯到所谓的吕库古立法,据说在吕库古制定的法律中,就包括了对拉科尼亚以及美塞尼亚的土地进行平等分配。事实上,斯巴达人的土地分配一点儿也不平等,而且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平等。与希腊的其他城邦一样,斯巴达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穷人和富人。
斯巴达和其他一些城邦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明显而且变得越来越敏感的差异在于:如果一个斯巴达人太穷以致无法向他所在的“公餐食堂”提供法定的最低份额的农产品的话,就会被剥夺作为“平等者”的资格,并且成为一个“低等人”(Hupomeiones,Inferiors)。这样的自动降级处理反过来又越来越严重地削弱了斯巴达军队的实际力量,而之前正是在这支军队的保障之下,直到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斯巴达在希腊世界内外还一直保持着强国的地位。然而,在斯巴达,土地被大量集中的确切机制到底是什么(现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辞与古代文献对此所作的不同描述是一样的)?
斯巴达军队中人员短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250年的这段时间里,斯巴达公民的数量从3000人降到700人,而且,其中仅仅只有100人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这就是阿吉斯决意要进行改革时斯巴达正面临的可怕状况,他重新打出了由来已久的、用来团结被压迫农民的旗号;废除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这种改革本身就象征着斯巴达正在变得越来越“正常化”(normalization),而改革的内容却与这种变化是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