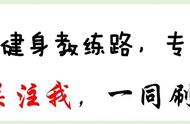阿之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曾经,天水围是个让我充满好奇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中,它被蒙上一层浪漫的面纱,它和九龙城寨、笼屋、重庆大厦一样,是香港特有的产物,在这片井然有序的弹丸之地,它们于边缘地带杂草丛生,藏污纳垢且藏龙卧虎。后来和在香港从事了多年城市规划工作的好友深聊过才知道,想象毕竟只是想象。天水围曾被作为“规划失败”的案例遭遇口诛笔伐,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就是根据发生在天水围的真实案件改编而成。
在毛骨悚然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之前,许鞍华曾经拍过一部温情脉脉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对于许鞍华而言,后者只是前者的铺垫,真正的重头戏还是想把这起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搬上大银幕,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没承想低调而寡淡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上映后在业界和坊间都赢得赞誉声一片,更横扫当年各大华语电影颁奖典礼,在奖项上满载而归。这一切,都让重口味的《天水围的夜与雾》反倒有些黯然失色。

把《天水围的日与夜》影像化的过程颇有戏剧性。在该片编剧吕筱华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求学之时,她将写好的剧本寄给当时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许鞍华,剧本的故事背景设置在荃湾,讲述香港普通老百姓平淡生活的点滴。剧本寄出去后便石沉大海,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吕筱华也从事了一份和电影毫无关系的工作,几乎忘记她还曾经创作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她因为该片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言语之间满溢着无心插柳的惊喜。
其实许鞍华并非不想把这个剧本搬上大银幕,只是苦于找不到资金。直到后来王晶决定注资,正在筹划《天水围的夜与雾》的许鞍华,把吕筱华的剧本故事背景从荃湾改成天水围,为的是给那起即将被影像化的灭门惨案做个柔和的铺垫。所以《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展示的,是个“非典型的天水围”,并非大众口中的“悲情城市”,因为它本就不是发生在天水围的故事。

我最初对天水围的想象,也来自于这两部电影的反差,是什么样的地方,既可以让挣扎求存的草根阶层散发出人性的光辉,又潜藏着如此触目惊心的罪恶。虽然后来也知道,前者的美好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但这正也是人们喜爱这部电影的缘由。尽管从荃湾搬到天水围,可《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故事逻辑,却和现实中的天水围是贴合的——基础设施简陋、工作机会稀少、精神生活贫乏,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与自己和谐相处是门大学问。
但既然这本就不是发生在天水围的故事,电影中的天水围多大程度地接近事实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影片呈现的人性之美。描写底层民众的文艺作品,常常跳脱不开僧多粥少的困境,需要用大篇幅地着墨一群挣扎求存的人,如何抢夺有限的资源。《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并不乏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细节描写,然而和电影配乐一样,这些细节都只是影片的底色。与天水围的匮乏形成对照的是,影片中生活在天水围的人,无不宽容、隐忍、念旧、互助、无私,这些人性的美德并未透过非常戏剧性的事件和场景加以呈现,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散落在影片的各个角落里。

影片以鲍起静饰演的贵姐在超市的工作为开端。乍一看贵姐和上了年纪的普通蓝领工人并无太大区别,超市也是日常生活中的超市,但随着影片的推进会发现,超市的场景,某种程度是“孤岛”的隐喻——工作时的贵姐,被水果摊子环绕,在果摊上亲力亲为、精耕细作她的一亩三分地,下班后脱去工作服,她和天水围的其他师奶一样,也需要货比三家地选购蔬蛋及肉类,跨出自己的主场水果摊后,超市的其他部分,于她都是客场作战。
早年丧夫的贵姐独自一人带大独生子张家安,从她与儿子以及其他晚辈的年龄差距来推算,贵姐晚婚晚育,且年少时因为帮补家计、供弟弟读书,她十四岁就出来当学徒。她个人的成长轨迹终究敌不过时代的迅猛发展,没有一技之长的她,被远远地甩在时代的末端,只能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
年少时被她供养过的两个弟弟,发迹后都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住在匡湖居富人区的他们,从未忘记过报恩。但习惯于自食其力的贵姐,在不占亲人便宜这件事情上显得过分较真,牌桌上帮弟妹打麻将输掉的钱、中秋节弟弟家送来的月饼券,她都锱铢必较,必须自己掏腰包才安心,表面上大家庭共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生活中的贵姐和工作中的她一样,将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很难和亲人产生实质性的情感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