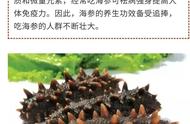“门罗主义”漫画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原因。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已经把美国的西部扩张也纳入了考虑,他担心如果和英国一起回应“神圣同盟”,美国将来扩张时可能会受制于英国,无法排除其干涉。英国非常善于用联合签署的文件来牵制别人,比如在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俄国沙皇兼任波兰国王,后来沙皇决心修改波兰宪法,英国就以维也纳会议参与者之名出来阻止,说波兰宪法怎么写是维也纳会议定的,你不能单方面改变。这就让我想起,前几年英国以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片面解释为依据干预香港事务,也是类似的操作。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儿子,做过大英帝国臣民,知道英国是怎么玩政治的,因此对英国抱有很深的戒心。所以,钱伯斯的《唯利是图》部分回答了美国不与英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原因问题,但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门罗主义”起源的全景。
前述美国“门罗主义”的二元性,可以关联到卡尔·施米特在二战之初对美国在凡尔赛和会持有双重法律标准的批判。有国内学者表示,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冷战两极都可归为美式普遍主义的新“门罗主义”,真正符合施米特期待的争取大空间的“政治觉醒的民族”只能在两极的夹缝中成长。您在书中对施米特提出了一些批评,认为他用空间性压倒了时间性,没有充分讨论资本主义发展与“门罗主义”演变为干涉主义的关系;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施米特的理论建构割裂了政治性(the [geo]political)和社会性(the social),他的批判依然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您认为对于施米特理论可以火中取栗吗?
章永乐:我在《此疆尔界》第二章《中欧的“拦阻者”?“门罗主义”、大空间与国际法》最后有一句话:“……他终究将重心放在政治神学和法学上,而没有对德国从十九世纪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到二战期间的‘战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做更多的论述。”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里指出,“政治”不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并行的一个单独的领域;各领域中斗争到了一定烈度,产生了敌友区分,因而才上升为政治。这个论述包含了深入探讨“经济”与“社会”的“政治性”的潜在可能性。西方晚近的一些理论尝试正是抓住了这个切入点,试图激活施米特的理论,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但施米特个人在经济社会政策上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哈耶克很喜欢引用施米特,两个人在反对魏玛“行政国家”上,可以说是有很多共同语言。施米特并不寻求从根本上反思资本主义逻辑本身,他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普遍主义阶段后在政治上的表现。但问题就在于,有什么因素能防止资本主义从一种较早的形态发展为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形态呢?靠“民族精神”么?我们看到,德皇威廉二世大讲“世界政策”(Weltpolitik),试图学习大英帝国的全球帝国主义;一战之后德国精英放弃了“世界政策”,执着于经营“中欧”区域。“民族精神”是无法解释德国执政精英的策略和话语变化的。德国执政精英究竟是追求全球霸权还是区域霸权,实质上是基于既有的实力做出的战略选择,从列宁的眼光来看,其实都是“帝国主义”的表现。

卡尔·施米特(1888-1985)
施米特对“时间”与“空间”都非常敏感。我认为他是有意地拒斥了在时间-历史维度上的一种理论发展路径。在施米特的理论逻辑当中,像“先进性”“先锋队”这样的概念是比较难出场的。《宪法学说》(Verfassungslehre)第八章对苏俄革命与制宪的讨论,说明他的理论逻辑不能容纳“先进性”以及对未来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的观念——这种观念和他的“拦阻者”(ὁ κατέχων,源于《新约》中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神学概念是矛盾的。施米特认为冷战时期的两大霸权都代表了伪先知“不法者”(ὁ ἄνομος)的力量,因为它们都指向了历史的终结和全球一统的前景,但以人类为统一单位将取消基于敌对关系的政治本身,这就违反了《旧约·创世纪》中上帝的教导。他认为德国应当扮演对抗“不法者”的“拦阻者”角色。既然无法接受时间-历史的“先进性”,施米特只能先从人数入手,讨论行使“制宪权”的群体在全国人口中是多数还是少数,但这样就无法阐述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逻辑。我认为,我们当然首先还是要从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行动者自己的思想论述和实践行动,来理解新中国的立国精神。
您在书中指出,“门罗主义”的全球“翻译”之旅,一方面与预设美国为听众有关,一方面和地方转化有关,比如“门罗主义”在亚洲被简化为“XX为XX人之XX”的口号,就与古代汉语表达“天下”归属的句式发生了共鸣。您说“五四”运动是对日本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回应,并分析了中国不同的文化-政治精英对日本及其“门罗主义”话语认知转变的过程。在您看来,近代不同群体对日本由爱到恨的变化,有什么殊和同?
章永乐:中国在近代沦为了东西方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从晚清到民国,从李鸿章、伍廷芳到蒋介石,不少政治精英的基本意识是中国的领土完整依赖于列强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甲午战争后,日本被许多人期待扮演欧洲列强牵制者的角色。尤其是1897年以来,欧洲列强在东亚的侵略骤然加剧,德国占领青岛,俄国占领旅顺,英国占领威海卫,美国占领邻近中国的菲律宾,东亚面临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危险。而日本则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利益受损,对欧洲列强有很大的怨气,它积极游说清政府高官改善对日关系,吸引了大量中国地方精英和官员子弟留学。那一阶段,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有许多精英人物在日本活动。近卫笃麿领导的东亚同文会几乎一统之前的“兴亚”组织,跟中国的两派人士谈笑风生。近卫主张的“亚洲门罗主义”因此名噪一时。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打,中国大批知识精英为日本呐喊助威,并为日本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日本的“亚洲主义”叙事正是在这一国际形势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部分精英提供过一个暂时的集体认同。

近卫笃麿(1863-1904)
这一局面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主要原因是列强在华力量对比逐渐失衡。尤其在一战期间,欧洲列强聚焦欧战,减少了在华资源投入,日本的影响突然蹿升,甚至向中国强加《二十一条》。这一下让中国精英感受到了日本带来的巨大压力。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的皖系政府从日本获取了“西原借款”,试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这就将许多地方实力派推到了对立面。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也试图寻求日本支持,但屡遭挫败,最后只好在反对皖系的同时也反对日本。1919年的“五四”运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内各派联合起来打击皖系,在这个过程中,山东问题起了导火索的作用。皖系经过“五四”运动的削弱,最终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落败。因此,中国精英态度发生变化,主要还是和日本在华势力增长有关。当日本弱的时候,它讲“亚洲”认同,反对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确实感召了很多中国精英,但在它强了之后,它的行为表现让很多人意识到,它和欧洲列强没有根本区别,甚至更危险。

竹内好编日本现代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卷(1963)
梁启超是比较早看清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本质的。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日本读了许多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和文章,1903年考察美国又让他进一步深化了对美国的认识。他说美国的“门户开放”是“灭国新法”,并意识到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相比之下,不少同时代人要等到时势大变之后才改变想法。比如说,孙中山早年在表述中对日本的“亚洲主义”多有响应,其反袁的“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都寻求日本官方和民间支持,在1917年开始的护法运动中也对日本有过一些期待。但是,日本支持的是段祺瑞政权,因此孙中山只好寻求和其他力量结盟。1918年,孙中山试图与德国、苏俄建立一个同盟,未果。1923年,他在苏联的帮助下,与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1924年他重新解释“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基于“黄白种争”的“大亚洲主义”决裂。他倡导的是一种基于王道/霸道之辨的“大亚洲主义”,而当时的苏联,在他看来恰恰是行“王道”的。这可以说是时势推动思想的发展。
您在书中的一个注释里说,对“门罗主义”的关注贯穿了*的一生。您能谈谈游击战和运动战思想,以及“亚非拉”框架与“门罗主义”的关系吗?
章永乐:*早年喜欢读梁启超,文风受到梁启超影响很大,以致引起他在湖南四师的老师袁仲谦的不满。*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袁老师认为他模仿的梁启超“新闻体”半通不通,要求他改变文风,于是*只好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鉴于梁氏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谈论“门罗主义”,外加一战期间美国宣传在中国公共舆论界带来的“门罗主义”话语的能见度,*受到这一话语影响,并不奇怪。但*一开始是反对“湘人治湘”的。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萧子升信》中分析湖南政局,认为湖南都督汤芗铭(湖北蕲水人)被驱是湖南的不幸:“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7月25日*再次致信萧子升,概括前信内容为“言湘人取们罗主义以便其私”,并明确表示湖南不断杯葛外省籍官员,造成“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但到了1920年,*成为“湖南自治运动”的先锋,赞成《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提出的“湖南们罗主义”,推动“省宪”的制定。不过,在短暂的“湖南门罗主义时刻”之后,*很快走上了另一条救国的道路。1921年7月,他登上了嘉兴南湖的红船。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以“石山”为笔名撰文《省宪下之湖南》,已经是对“湖南门罗主义”进行批判了。
在国共合作启动后,“门罗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变成一个负面词汇,意思是搞封闭的小圈子,不讲大局。在党内,“门罗主义”更多被用于谈论国际事务,党内事务中基本不用这个词,我在书里列举了几个例外案例,但没有发现更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凭借游击战和运动战,实施“红色割据”,但这种“红色割据”和军阀的地方割据有很大差别。红军能够在不同军阀的势力范围之间生存壮大,依靠的正是不断打破既有边界,在敌人的辖区动员起民众力量的能力。穿越边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本身就是对军阀的“门罗主义”的克服。而要保持这种穿越边界的能力,革命政党就需要克服自己内部的利益集团化、宗派化的倾向。党内习惯于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而非“门罗主义”指称这种现象。我想这与革命队伍的人员主体变成了农民有关,党内、军内交流需要使用农民能接受的语言。“门罗主义”就显得太洋气了,用“山头主义”描述“占山为王”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更加形象,更能反映根据地的生活经验。
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也主要是在“超国家”层面使用“门罗主义”这个词。1940年,他在《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的报告中,对美国做出评论:“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意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因为美国手伸得太长,容易得罪其他列强,所以当时的中国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他在这句话里区分了“门罗主义”和“世界主义”,这实际上是接续了梁启超与蔡锷早年在《清议报》上对“门罗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作的辨析。上面说过,主席在1920年讲过“湖南门罗主义”,这里的“门罗主义”是一个具有防守色彩的概念。他在这里还是接续了这个用法,将美国主张两洋利益的扩张性姿态称为“世界主义”。1958年,*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后以彭德怀名义发布),抨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第二年他在接见日本友人时,也讲过类似的话:“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这是“中国式门罗主义”吗?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能成立。这里的表述只是强调区域自主,强调美国不应干涉西太平洋事务,但并没有说谁在西太平洋起主导作用。
与这些表述密切相关的,是建立“亚非拉”这一全球性反帝联盟的主张。1960年,*总理在接见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时,提出“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这里重点在于,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自主与其他国家展开经济交往,摆脱美国控制。美国人讲“门罗主义”,尽管在修辞上会承认别的国家的自主性,但它又有一套很神奇的操作——我可以为你的自主性代言,认为你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自主,我帮助你排除外来障碍,让你“自主”起来。这就产生了以“反干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中国当时的“亚非拉”框架里没有这一逻辑,没有“其代予言”的冲动,一直强调的是当地人民立足乡土,自己组织起来抗击帝国主义,自己争取独立地位,外部的援助是次要的。我想关键就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靠莫斯科“输血”输出来的,那么当中国去评论其他国家的革命的时候,也会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靠自己摸索出路。
从您已经出版的三本著作的标题看——“邦”“国”“疆”——您持续关注着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问题。《此疆尔界》虽然重点讨论边界和空间,但也试图论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我们党史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克服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和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为什么您如此执着于国家建设的问题?
章永乐:有学术建制的原因。虽然我的问题意识是高度跨学科的,但我的学术绩效考核是在法学院做的,所以倾向于先在那些有可能和法学结合得比较紧密的研究议题上发表成果,而“国家建设”既与宪法相关,也与国际法相关,比较容易出与制度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果我是在历史学系或政治学系的绩效考核体系下,发表的优先顺序也许会有所不同。
我的三本书不仅讨论了“国家建设”,其实还讨论了“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尤其在第一本书里,这个维度还比较突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包含着两个维度: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反封建”与“反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面临着东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力,要通过“旧邦新造”来获得独立自主,这需要建设共同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更强有力的财政-军事体系、更合理的权力配置和更有效的行政组织,等等,这是国家建设的内容;但同时,在一个严格区分“内/外”的民族国家时代,中国的内聚力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共同体自觉。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的东亚朝贡体系空间秩序,基于亲疏远近关系,并不需要“内/外”分明的民族共同体自觉,但在中国被迫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体系后,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就很容易成为基于西方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经验的新政治知识体系的攻击目标。近代以来,许多欧洲人将中国视为一个内部充满异质性、可以拆解的“帝国”。这个逻辑感染了近代日本,哪怕是主张“保全支那”的日本“亚洲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保全”的,不过是不包括“满、蒙、回、藏”的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顾颉刚在1939年驳斥过“中国本部”这一概念)。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根据亲疏远近,同周边藩属形成充满弹性的政治关系的统治秩序,在这个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基于既有的疆域,形成“中华民族”的自觉,这本身是对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时代的回应。
欧洲从封建秩序经过绝对主义时代,到最后形成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逻辑并行的局面,发展过程是渐进的。在那些享有列强地位的欧洲民族国家内部,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解决阶级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并不需要回应外国控制和压迫的问题。这一局面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很深的影响。比如说,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就曾经以“民族自决权”为焦点展开辩论,列宁力主“民族自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考虑到了亚洲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认为支持被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获得独立,是这些地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卢森堡担心支持“民族自决”有可能造成“节外生枝”,为无产阶级的横向联合设置了新的障碍。卢森堡的思考有更多的欧洲历史经验基础,而列宁则是将亚洲革命的视野与欧洲革命的视野结合起来,将发展的不平衡与殖民主义压迫问题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在列宁的支持下,国共两党合作启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多重任务,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国家建设水乳交融。比如说,在延安时期,我们一方面看到从“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实践,看到面对根据地税基薄弱的基础条件“开源节流”、推动军事-财政机制和行政组织合理化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又能看到推动民族平等,呼吁国内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举措。就社会革命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二十世纪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都不可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同日而语。而这一差异也解释了中国后来为何能够在冷战格局下不随美苏两霸起舞,而是自主设置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议程,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对西方“自主性开放”。也正是由于中国在二十世纪革命与建设中锤炼出来的这种自主性,中国对外开放但不陷入“依附”。当中国的华为公司面临美国“长臂管辖”的打击的时候,能够避免重蹈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覆辙,依靠的就是这种自主性。在今天,当我们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仍然需要回到中国在二十世纪所打下的自主性基础。因此“国家建设”始终是重要的议题,但我们需要将其与“民族建设”、社会革命等结合起来思考。
您上一本书的主角是康有为,尽管《此疆尔界》没有花太多笔墨讨论他,但康氏重新阐释的的公羊学“三世说”,尤其是以某种区域霸权作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过渡的担当者的设想,无疑与“门罗主义”有一定相似性。您强调,“康有为的保守,其基础在于历史进步论前提下对于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此疆尔界》里,您分析李大钊时也说,后者设想的“新亚细亚主义”是“全人类走向平等联合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康有为和李大钊的“过渡”都体现了他们思考中超越国家的未来指向,对此您怎么看?康有为一生有各种误判,终逆势而败,为什么还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