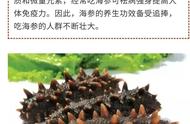《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败》,章永乐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出版,230页,48.00元
章永乐:我主张区分“问题”与“答案”。历史上一些人物擅长于提出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他们的答案却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推敲他们的答案。康有为在清末力主君主立宪,在辛亥革命后仍不改初衷。但他没有从基本原理上否定共和,只是认为共和之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超越发展阶段的政治选项。在他充满进步论色彩的“三世说”框架中,君主立宪制适合于“升平世”,将在未来的“太平世”被共和制度取代。康有为对中国具体情况所下的判断有内外两方面的依据:一战前的国际体系确实是君主制主导的,欧洲基本上是君主国的天下(除了法国、瑞士等极少数例外),美洲虽然是共和国为主,但国际影响力较弱,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恰恰是国际体系中的少数派。而在君主制崩溃后,中国的政治整合又出现巨大问题,就好像系统转换,原先的系统卸载了,新系统却不能马上正常运转,于是乱象纷呈。康有为对此作了很多深刻反思,但他提出的药方无疑有很大局限。在他看来,君主制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一套公开承认不平等的荣典制度,凝聚起一支核心领导团队,从而获得比共和制更强的整合能力,而讲平等的共和制就缺乏这样的荣典体系可用。但问题还是,君主该如何产生?欧洲君主制非常讲究血统的纯正,没有血统证明,要争夺王位,就会被视为僭主。但好处在于,欧洲各国的王族相互通婚,论起来多少有点亲戚关系,一个国家需要君主,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王族里找人。康有为熟悉欧洲的这个体系,认为即便严分满汉,让满人充当君主,至少也是符合欧洲惯例的。然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传统恰恰没那么讲血统,讲的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像朱元璋这样社会底层出身的人也可以当皇帝,关键还是看是否具备统治的能力,能否在“天下大乱”之后恢复和平和繁荣。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最高权位的竞争者范围是非常广的,清朝皇帝退位了,地方军阀里想自己当皇帝的人多的是。民初地方实力派掌握军权财权人事权,抵制种种中央集权举措,不仅不利于共和制的巩固,甚至也不利于君主制的重建。那样一个政治结构很难形成支持君主制重建的军事基础。袁世凯想称帝,北洋集团内段祺瑞、冯国璋等高级将领就没法接受;至于支撑溥仪复辟的军事力量,更是比袁世凯的军事力量要弱得多了。我在《万国竞争》中讨论了康有为的更多误判和实践失败。

康有为(1858-1927)
再来说说超越国家的未来指向。中国在近代被迫进入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体系,并且被归入“半文明国家”,屈居自诩“文明”的列强之下,这让许多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有深深的挫败感。于是,他们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适应这个秩序及其逻辑,又不甘心完全被它同化。更确切地说,先适应,后超越。所以他们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建设上展开论述,另一方面还会设想终结列国并立、重归一统的远景。就后者而言,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换言之,通过一种时间上的处理,他们试图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新凸显中国的主体性。在康有为《大同书》设想的全球一统前景中,全球“公政府”设在葱岭,也就是部分位于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全球通行语言文字重点参考汉语;全球被划分为“百度”来治理,有郡县制色彩,但实行自治。可以说,这是近代较为典型的因应时势的知识反应。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路向,比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发表的一系列后来被汇集为《新民说》的文章里表示,竞争为文明之母,如果竞争终止,文明就会退回到野蛮,因此我们必须将国家设想为最高的团体,因为如果有比国家更高的团体,竞争就会丧失。这个强调竞争的逻辑部分源于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概略论》,福泽谕吉则是受了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和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的影响。这就是十九世纪欧洲典型的文明论论述:欧洲之所以强大,因为它多元自由,在竞争的推动下,长出一个丰富的文明。梁启超由此批判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扼*了竞争,使得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发现欧洲这个提倡竞争的列国体系最后导致国家之间猛兽般的撕咬,直至爆发世界大战,上千万生命灰飞烟灭。于是他很快转向贬抑竞争,讲“互助”,讲社会主义精神。他说中国要支持国联,因为中国有丰富的“超国家”政治传统,可以上溯到春秋五霸的会盟。这个姿态和康有为就比较接近了,《大同书》写“去国界”的时候,是明确写过春秋的会盟的。

章永乐摄于康有为在瑞典沙丘巴登购买的饭店岛前,2020年。
与梁启超相比,李大钊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他在青年时代的知识结构中,比梁启超有更多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些思想往往也设想了列国并立消亡的前景。一战时期,美国的联邦制和“门罗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制度性依托,威尔逊提出国联设想,更是带动不少中国论者思考世界经过区域化进程而走向统一的前景。而类似的想法早在《大同书》里就出现了。康有为设想在“升平世”,德国统一欧洲,美国统一美洲,中国或日本统一亚洲,列强的殖民地也不必独立,而是直接并入新的区域联邦结构,帝国成了促进大一统的中介。李大钊在一战期间和战后时期非常关注大斯拉夫主义、大日耳曼主义以及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等思潮,他和康有为都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吸纳吞并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政治单位的倾向,康有为想利用这一趋势,加速历史进程,李大钊的态度则是,认同全球一统的方向,但反对武力压迫与吞并的手段,他尤其警惕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威胁,认为亚洲各国在解放的基础上自主联合才是正途。他甚至将国内军阀的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与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相比较,认为双方具有同样的扩张主义逻辑。而他最终认同以自下而上的民众革命,来克服军阀的“门罗主义”。这其实就是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道路。
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写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源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植根于近代先贤在列国时代探寻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努力之中。《诗经·周颂·思文》云:“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适应严分疆界的列国时代,但同时始终保持“无此疆尔界”的情怀,这是近代先贤传递给我们的思想位置。
《旧邦新造》是一部宪法史著作,《万国竞争》《此疆尔界》分别对应了思想史(“政治语境之基源式研究”)和概念史(“话语全球传播史”)的方法。鉴于这三本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有重叠,您能谈谈您论述方法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吗?

《旧邦新造:1911-1917》,章永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293页,45.00元
章永乐:这三本书都是跨学科的著作,但都包含着对法律问题的讨论。它们都不以法院及其判决为研究对象,而是关注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与国家政体的权力配置,关注立法理念和立法文本(如国际条约、宪法与宪草文本),关注政治过程中的法律辩论——这种辩论通常没有哪个权威机构给予一锤定音的正式裁决。我会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思想者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立法者,考察他们的思想中的制度方案,以及他们思想带来的制度后果。
如何研究政治过程中的法律辩论和法律论证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在政治过程中,要“师出有名”,就需要为自己的诉求提供规范依据。法律文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在“正名的政治”之中,可以有几方面的功能:一,限定讨论的议程,比如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其争议的范围就受到《临时约法》的限定;二,提供规范性诉求的具体依据,比如黎元洪与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的具体诉求,就需要征引《临时约法》中涉及权力配置的相关条文并予以解释;三,作为正当性象征符号。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他组织的护法军政府完全不是按照他主张维护的《临时约法》组织的,但即便在不引用任何条文的情况之下,《临时约法》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仍然发挥了某种“正名”的作用。1922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直系宣布“法统重光”,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就是为了和南方争夺这个正统的象征性符号。至于“门罗主义”,即便在美国本土也是一个介于国际法原则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理念,其解释和再解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后,其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是异态纷呈,影响了很多宪法主张和国际法主张的提出。我喜欢研究这种没有权威机构给予标准答案的规范性争议,因为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可以呈现历史中包含的多种可能性,同时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探索的快乐。但同时,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不得不交叉使用不同的方法,而不可能用一把大刀从头砍到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