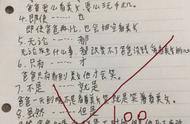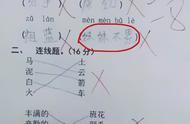1923年3月8日下午,俞平伯动身前往白马湖。此前俞平伯接到朱自清的信,邀他到白马湖的春晖一聚,恰好前不久俞平伯刚刚辞去上海大学的教职,闲来无事,便搭乘新江天轮从上海出发,3月9日清晨到了宁波码头。一下船便赶上大雨,俞平伯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在雨中奔跑,像雨中的马,还好是南方的雨,但俞平伯还是多给了车夫一些钱。到了火车站,俞平伯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朱自清信中说在“百官车站”见,以为不太远,结果一买票吓了一跳,还挺贵,连二等票也要一元四角。雨中火车走了近三个小时到了百官站,月台出站却不见朱自清来接。下车的人本就不多,一目了然,雨还在下,待向人打听白马湖的春晖学校在哪儿竟无人知道,最后问一个街边剃头的人方知自己坐过了站,春晖学校在前一站的“驿亭站”旁。俞大惑不解,信中明明说的是百官站,但为何在百官站下而不在驿亭站下呢?怎么搞的?越发觉得荒诞不经,难道佩弦说了在百官站却在驿亭站等着?不可能再坐回去,又叫了一辆黄包车回返,车费两元,比宁波到这儿火车还贵,辗转到了春晖见了朱自清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我在百官站下车?为什么不来接我?
俞平伯完全不顾朱自清身旁的一干同事,怒不可遏,朱自清却不以为意一直笑着慢慢解释。朱自清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湿漉漉的俞平伯更来气了,解释到最后朱自清竟然说其实他也是坐这趟车来的——彼时朱自清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书同时还在宁波省立四中兼课,事实上两人就在一趟火车上。当天晚上,也就是1923年3月9日晚上,俞平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两个像小孩子似吵了起来。”
“吵”过了之后朱自清还要上课,俞平伯一时无事可干要听朱的课,朱自清也没反对。铃声响过坐在学生中俞平伯心静下来,听得蛮认真,下了课两人携手而归。翌日晚上,白马湖烟水淡淡,黄月亮升起,俞平伯应朱自清之邀在春晖中学湖畔礼堂为中学生做了一场题为《诗的方便》的讲演:
“我今晚虽讲说诗的方便,但诗实无方便可言。”
讲演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的总结富于哲理,洞若观火:
“诗固是生活的一部分,又是生活的一种综合表现——它是在生活中表现生活的!创作的成功每跟着个性的发达,不知不觉,一页一页地展开去,故作诗本无方便,从无方便国想个方便,是从做人下手。能做一个好好的人,享受生活的丰富,他即便不会作诗而自己就是一首诗。即便不是其价值,岂不尤胜于名为作诗的人。”
(不知现在的中学生能否听懂?)
有关这次讲演校刊《春晖》记载:“彼时白马湖畔的学校大礼堂窗外风雨交作,讲演声与风雨声相应和,湖上的诗景殊乎浓极了。”
一百年后——确切说98年——2021年9月26日,笔者与一干当代作家来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村依山傍水的春晖中学。中巴车载着一行从绍兴到了上虞的郊外,下车步行走了一段湖畔的煤渣路,四周是水乡景象。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直到此时我对春晖还一无所知,此前当听说要参观一所中学,说实话,心里还颇有些不以为然。谁还不知中学啥样子,大概是某种先进吧?只是客随主便,这里的风景倒还不错罢了。然而进了学校,看到满目旧建筑我才有些晕菜,此后一系列的惊讶扑面而来,仿佛是给我们这些所谓的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猛击一掌。如本文一开始所述,朱自清老师的旧居所展示的当年两位大家吵架的情景有趣而平常,这且不说,你道“吵架”时朱自清身旁的“那帮子同事是谁?”是夏丏尊、丰子恺、李叔同、朱光潜、匡互生——“五四”第一个冲进天安门赵家楼的人,都是春晖中学的老师,而来此讲演的则是蔡元培、黎锦辉、陈望道、黄炎培……
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我是说中学?

春晖中学旧影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春晖中学的学术气氛很浓,故居墙上显示:春晖中学的老师们都认为“日常授课只是教育方法的一种,欲竟知识全功,非兼向别方面不可”,为此一百年前的春晖中学经常定期不定期地举办专题讲座,或请校外方家名流,或由本校教师担任。据载校内的夏丏尊老师讲过《道德之意义》,朱自清老师讲过《刹那》,丰子恺老师讲过《贝多芬——月光曲》,朱光潜老师讲过《无言之美》,刘薰宇老师讲《牛顿和爱因斯坦》,匡互生讲《天空现象》……1923年5月蔡元培来到春晖,发表了题为《羡慕春晖的学生》讲演,开篇竟和学生以兄弟相称——
“兄弟在北京时,经校长(经亨颐——笔者注)时常和我谈起春晖中学的情形,原早想来看看。此次回到故乡,得和诸位相会,非常欢喜。”
关于那次讲演,《春晖》校刊第十三期记载:“此番蔡孑民先生因扫墓回故乡绍兴,特应本校经校长之邀来到春晖,经校长致欢迎辞——蔡先生道德学问久为全国人士所景仰,此番由兄弟相约,得承蔡先生躬临赐教,诸位务当细心恭听。”
怎么说呢?我对晚清,辛亥,北洋一向没好印象,如果不是这次活动完全不知道春晖,不知道一百年前这里的一切。
春晖是怎么回事?
就历史而言,我觉得我就像个白痴。
我这种作家有着怎样先天缺陷?
春晖中学像中学吗?但明明就是中学。1919年春晖中学由乡绅陈春澜出资20万银元所建,此前出资5万建了春晖小学。主楼为仰山楼,尖顶,拱廊,长方形,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从北面的象山俯瞰该楼是一个拉长的“山”字,取对知识读书“高山仰止”之意,西式建筑又是中国观念,自然,相得益彰。仰山楼对面是曲院,曲院为春晖的教师宿舍楼,由二层楼围成一院子,呈“凹”字形,38个大间,四个楼梯小间。还有图书馆。图书馆为一栋独立的希腊式建筑,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楼上是图书室,楼下是阅览室,阅览室又分内外,外可阅览报纸内可阅读杂志。漫步在春晖校园,看着“近代”的仰山楼,图书馆,曲院,一字楼,一处处故居,以及不大但对一所中学足够大的波光潋滟的白马湖,我不知自己究竟在想什么,脑子空空如也。虽说时光并未倒流但我觉得绝非在现实之中。我不想承认过去,过去又如此真切。

“长松山房”建于1929年,为经亨颐私宅。因屋旁有三棵高大的松树,取名“长松山房”。主楼为三开间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与主楼东西相连的是三间平房,为厨房和餐厅。东首还有两排前后并列的附属房。私宅建成后曾邀何香凝、陈树人、柳亚子、方介堪、张大千、黄宾虹等谈诗论文,切磋艺术,留下佳话无数。经亨颐离世后山房疏于管理,日渐颓圮,现仅剩遗址。

“晚晴山房”:始建于1928年,原址在“春社”西侧半山坡,系由夏丏尊、经亨颐、丰子恺、刘质平等人醵资为弘一法师(李叔同)所建禅居。1932年以前,弘一法师几次临白马湖居此。山房毁于抗战时期,1994年上虞弘一法师研究会募款易地重建并布置展览。2001年、2018年两次修缮布展。现辟为弘一法师纪念室。

“白马湖图书馆”始建于1922年,初名为“博文馆”,1980年扩建两间,建筑面积450平方米,楼上图书室,楼下阅览室。著名书画家陈衡恪题写“白马湖图书馆”匾额。曾辟为校史陈列馆,2016年恢复为白马湖图书馆,馆名由叶圣陶题写。系文保建筑。

“小杨柳屋”建于1923年,系春晖教工宿舍。因丰子恺当年执教春晖居住时在宅内墙角栽种杨柳而得名。建筑仿日本“玄关”格局,结构独特,小巧雅致。1925年,吴梦非居此时曾易名“蓼花居”。2018年重新修缮布展。现辟为丰子恺、吴梦非事迹陈列室。系文保建筑。
硬件倒也罢了——我们现在不缺硬件——主要那时一所中学竟有那么多牛人或在校任教或时来讲演,简直匪夷所思。中学教师不仅上课还要开讲座,日常上课与讲座并举,视野足够开阔,教育理念简直不知哪来的。而且不仅讲道德文章,也讲自由科学平等,甚至讲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上世纪二十年代也刚出名吧?百度云:爱因斯坦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在春晖我觉得某些历史被打通了,文明有时并不完全依赖于所谓历史而有独立的演进方式。白马湖的春晖难道不是一种文明的清晨?有人轻点我的后背,悄声说《荷塘月色》写的是白马湖,我一点不惊讶,此时我这个白痴仿佛更深理解了朱佩弦的月色。
还是看看墙上已故的人怎么说的,或许更能还原当时:
朱自清说:
春晖中学在湖有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连接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种着花。(《白马湖》)
丰子恺说: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人不晓得夏先生是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悼夏丏尊先生》)
朱光潜说:
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的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鼓励之下写成的。(《敬悼朱佩弦先生》)
顺便再说一下,朱光潜英文流利,多年后有学生回忆:一进教室,好像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英国人,全部用英语讲授。我们开始除了“yes”,“no”什么都不懂。提问题时,叫答者“stand up”或“sit down”也听不懂,他用手掌向上抬或手掌向下按才使我们懂了,但很快我们就被他那套听、说、读、写结合起来的,全方位的训练方法征服了。(责任编辑:孙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