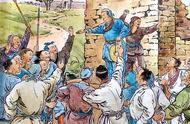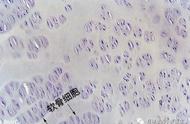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来看,李白作为一个有如此文学艺术成就的大文豪,他就算得不到上层官员的赏识,不能从事国家大事,在统治阶层中谋得一官半职,就怎么会有损于他最后在艺术上的成就呢?
但是李白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肯定知道他自己也是有才能的,也并非等闲之辈,要不然也不会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他自己最终的价值追求并不是在文学艺术上有所突破,而是希望得到上层的赏识,得到皇帝的青睐,能够辅佐君上,成就大业。

这种心态不是李白一人独有,中国传统文人包括现当代的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迥异于其他民族文学特质的“天下观”,宏大叙事虽然谈不会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向、落脚点往往要在这些地方着手。而且往往是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的东西。
而这就相应的削弱了他们对于自身文化艺术的重视程度,所以在文人看来,他们身上所擅长的这些笔墨文章,实在是不足挂齿的雕虫小技,比如苏轼曾就说自己“我书意造本无法”。

因此,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就给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带来无限的痛苦和折磨。一方面,他们所认为的文学艺术上的能力,并不能代表实际生活中、工作中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能力,但是这种认识随着科举考试僵化的文科性质而逐渐定型,让文人们相信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就等于自己的治国理政的才能。
因此,李白、曹植才会如此悲愤,杜甫一生也是如此,他诗歌写的这么好,却仍然不免于要落的一个穷困潦倒,客死西南的凄凉结局。整个古代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单一而不合逻辑,造成了无数文人的悲剧,他们本应该过的更加潇洒、更加自由,却被社会权力者所编织的大网紧紧的缠绕在一起,无法动弹。

所以,首先,这一逻辑是一种崇尚某些虚幻观念和形而上的儒家理念所推动的艺术交换,即我拥有才能,你正好这样规定,那么我这些才干理应该得到你的重视,得到你的赏识。
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所以,我生气、我愤怒,我感到自己怀才不遇。
因此,中国文人对于自己自身的评价,往往不是着眼于他们自身到底有无才干,而是着眼于他人,把评价自己高低水平的尺度交给国家机器,尤其是君王,如果君王赏识自己,重用自己,而自己又能干出一番大事业,那么自己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