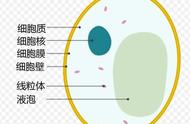顾心瑜

年幼时,最大的妄想的是和鸟儿一起乘风游荡。但身边的酸甜苦辣皆是拉着风筝的线,任我仰酸了脖子,终究自由不得。
直到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立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身影触动了我的神经。他无数次地将巨石缓慢地推向希望的山巅,再让它在哀伤的轰鸣声中滚向破灭。无穷无尽的推滚仿佛首尾相契的环形蛇,圈出命运的荒谬——这是众神给予他的惩罚,西西弗。
西西弗的生命是枯瘠的沙漠,连一片绿洲的意义也不得拥有,可他却背负着那块巨石的残酷刑罚,穿越了漫漫时光的风沙。抛却浪漫色彩与理想主义,他只是凡人,燃烧的激情终有熄灭的时候,坚强的意志亦敌不过这周而复始的劳作的损耗。为什么不舍弃石头,以极端终结一切?
听,听巨石的滚动声。那声响是一板一眼的节拍打奏,极有规律的齿轮运转,强健稳定的心脏跃动。沉入这样的声响中,我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朗,那个在鲨堡监狱里关了40年的老人。当他在垂暮之年终于走出了一生的桎梏,竟选择在安身之所自缢而死。无论监狱中的生活怎样寒冷刺骨,当他被那里的规则体制化,便再也无法出去重寻春暖花开的温暖。
西西弗沉默地继续推动石块,我却仿佛看见他背对着我,无言地翕动嘴唇。他说,人终究不能摆脱巨石的束缚,它是他的罪孽,亦是福祉。当接手巨石的那一刻,自己的生活已全盘接受它所订下的规则,无论这样荒谬的劳作是否有意义,它既已成为生命动力的源泉,他便不可置疑。质疑它,便是质疑自己的生。
他是西西弗,他是老布朗,他是我们,他是一切。每个人身上的那块巨石,或轻或重,它所承载的是我们的生。史铁生说“命若琴弦”,人生便是为了既定的目标而绷紧琴弦,弹出无数不同的音符。在舍弃石头的时候,最后一根信仰之弦断裂,老琴匠的生命之焰暗淡无光;在舍弃石头的时候,以死亡的空无换来的超脱,又有何用?
华灯异彩,歌舞流光,美食佳肴,书卷墨香,那块石头倘若是种灿烂的文化,便让人欣然接受,愉悦地沉醉其中;而沉重任务,繁忙劳作,甚至冰冷至一座监狱、一块巨石,也无需满心苦楚地喊着“要自由”。我们跋涉了一路,若不是主动挑选背上的石块,便是被动承担了石块。在本质上,人没有自由与否的区别,要活下去,就不可能干脆地舍弃石头,斩断一切牵连。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处处是限制,所以也就根本没有限制一说了。唯有坦然接受一切,才是真实的。
加缪写过:“朝山顶的挣扎就足以填满一个人的心脏。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快乐的。”我闭上双眼,看见幻化着无数张脸庞的西西弗,在奥林匹斯山巅上,有力地推滚巨石,向着那永不止歇的石头昂首阔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