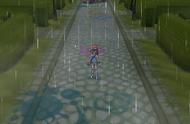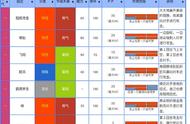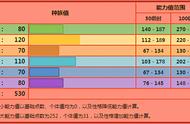沃纳·赫尔佐格。
近期,德国电影大师沃纳·赫尔佐格先后来到香港、北京和上海与影迷进行交流,三地也都举办了赫尔佐格回顾展,将最新修复的几部重量级作品搬上了银幕。
赫尔佐格是一位相当多产且在纪录片和故事片两个领域均有极高成就的导演。他曾多次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其中1975年首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时就凭借《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获得了仅次于金棕榈的评委会大奖。去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又为赫尔佐格颁发了黄金马车奖,以表彰其对电影矢志不渝的探索。
赫尔佐格几十年的创作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有充满矛盾的地方。不过,与其说是静态的“矛盾”,不如说是动态的变化。毕竟,他在长达五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中拍摄了70多部影片,至今仍在探索。正因如此,任何一篇文章、一本专著大概都不可能对赫尔佐格进行完全系统的梳理,就在我们仍然埋头观看这些几十年前旧作的时候,赫尔佐格已经又有两部新片走在路上了——追随赫尔佐格永远是一件难事,他健步如飞,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将会把我们和电影带向何处。
自然与征服:以上帝之怒迎战原始和混乱
沃纳·赫尔佐格以他的“双脚”闻名于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恐怕是世界上唯一足迹遍布所有大洲的导演,包括南极洲。他关注自然,同时也关注那些在自然环境中挣扎着生存下去的人。他们心中充满征服的*与对未知的执念和迷恋,无论是在沙漠、丛林还是雪原,都试图凭借自己强大的权力意志达成某种目的,最终的结果也是惊人相似。
对赫尔佐格来说,自然和征服是一组矛盾的关系,尤其是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近代世界史中,征服往往意味着对自然的利用、掠夺和侵犯。不仅如此,“自然”和“征服”这两个概念本身也蕴含着矛盾。他既认为原始的、自然的东西无比混乱,可以吞噬一切涉足的人类,但同时又深受感召。与此对应,赫尔佐格一方面在影片中不断强调人类在向自然迈进时所呈现的无比顽强的生存意志,另一方面也反复申明人类文明,尤其是工业化文明在面对自然时的乏力。
正如他在莱斯·布兰克为《陆上行舟》(1982)拍摄的纪录片作品《电影梦》(1982)中说的那样,“这好像是一片受到诅咒的土地,任何胆敢踏入其中的人都要分享这个诅咒。……这是一片上帝——如果存在的话——用他的愤怒创造出来的土地。……仔细观看的话,这里存在着一种和谐,是一种大型集体谋*所制造出来的和谐……。面对这样巨大的不幸,我们只能保持低调和谦逊。”在赫尔佐格看来,自然空间中充满致命的威胁,而人类的征服往往只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悲壮而无用的努力。

《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剧照。
赫尔佐格的剧情片中,原住民通常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象征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始之力,但他电影中对原住民形象的刻画并非一成不变,矛盾心态中的两方也在此消彼长地发生变化。比如在他最初也是最著名的作品《阿基尔,上帝的愤怒》(1972)中,原住民及其所藏身和象征的自然是危险、神秘且不可理喻的,我们看不到除了两个印第安人之外的原住民,船上的人却不断被从两侧雨林中射出的长箭*死。一种神秘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弥漫在整部电影当中。到了十年后拍摄的《陆上行舟》中,原住民虽然还是不可抗力,甚至在背后操控着菲茨杰拉德一行人的所有行为,但两种文明终究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交流。及至纪录片《苏弗雷火山》(1977)及其后的《白钻石》(2004),赫尔佐格对自然的敬畏仍在,但那种危险的氛围退去了,原住民此时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原始从容”和智慧的化身——正如当赫尔佐格向《白钻石》中的原住民马克·安东尼询问是否能在一滴水中看到整个宇宙时,对方的回答出人意料的诗意而震撼:
“我听不到你的言语,因为它如雷声贯入我的耳中。(I cannot hear what you say, for the thunder that you are.)”
究竟是什么在不断改变着赫尔佐格对自然和原住民的看法?更进一步说,为什么赫尔佐格会如此关注自然和征服这组关系,而并不像1960年代初发轫的德国新电影运动中的其他成员,尤其是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和沃尔克·施隆多夫那样集中描绘德国战后体制、政治与人的密切关系?
对笔者而言,很大一部分原因要从他的童年经历中去找寻。赫尔佐格出生于1942年二战期间的慕尼黑,在他刚出生之后不久,邻居的房屋被炸毁,赫尔佐格家也受到了波及,一家人搬到了德国与奥地利边境附近的小村庄扎赫兰。和德国新电影四杰中的另外三人不同,赫尔佐格从童年开始就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徒步旅行的爱好也是从那个时期养成的。所以,赫尔佐格几乎在刚有自我意识之时就开始了对自然的思考。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赫尔佐格为什么会在他的职业生涯和电影中不断强调“运动”的重要性,因为“运动”正是自然和征服的孩子。

事实上,赫尔佐格本人就是一名运动健将(应该说赫尔佐格也是一个“征服者”,他的自取名“赫尔佐格”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公爵”,充满着支配和权力的含义),除了徒步旅行之外,他还喜爱滑雪,尤其对团队运动有强烈兴趣。在《赫尔佐格自画像》(1986)中,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对滑雪运动的迷恋进行了回顾,甚至在其早年专门为滑雪运动员斯泰纳拍摄了纪录片《木雕家斯泰纳的狂喜》(1974) 。对赫尔佐格来说,运动能让人锻炼体魄,也能让人增长见识,更重要的是运动可以让人对空间的构成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见2018年3月赫尔佐格CFA讲座),这些侧面无疑都在他日后的电影制作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明和人性:在社会和战争中书写人类局限
尽管上述这些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影片某种程度上“定义”了赫尔佐格电影的题材和风格,当通观赫尔佐格的创作生涯就会发现,真正以自然与征服关系为主题的影片并非多数。赫尔佐格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自然”,而是一个来自文明外部的批评视角,它可以是人类学的,可以是宗教学的,甚至可以是科幻的;于他而言, 当面对某些远远超出认知范围的东西存在时,人类一定是渺小而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