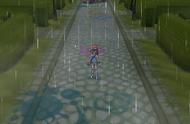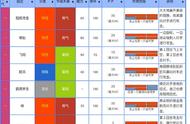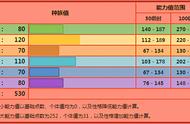《灰熊人》剧照。
从1990年代开始,赫尔佐格开始转向大规模纪录长片的制作,其职业生涯中几部重量级作品都是在这段时间拍摄出来的,其中又以《灰熊人》为其这个时期纪录片创作的巅峰。在讲座中,赫尔佐格提到自己在获得这个项目的消息时,立马从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制片人那里抢了过来,事实证明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把控确实超乎常人。通常来说,一个“人与动物”题材的纪录片会被拍成一部环境和动物保护题材的电影,但《灰熊人》则另辟蹊径地通过提摩西·崔德威生前提供的素材不断向人性深处开掘,去寻找他与动物为伍的终极原因。在这个过程之中,赫尔佐格没有对原始素材进行剪裁,而是把提摩西·崔德威不断重复的“表演”纳入到影片之中。
赫尔佐格对“重复”的偏好也显现在他的几部短片如《最后的话》(1968)、《警惕害马人》(1969)和《一只土拨鼠能啃掉多少》(1976)(这部影片所展现的拍卖过程也化用在《史楚锡流浪记》里)里。正是在不断的重复过程里,观众得以发现社会、语言的异化,达至某种赫尔佐格想要表达的“真相”。也正是透过这种方式,《灰熊人》不断展现出此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人类的狂喜和内心的风暴”——并最终发现其被熊吃掉的“真正”原因。不可否认,《明尼苏达宣言》所宣誓的纪录片制作方法至今仍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但确如赫尔佐格自己所说,他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思索“何为真相”这一问题,所以或许当我们还在奉行《宣言》之时,赫尔佐格早已进入了下一个无人之境。
宗教和超验:赫尔佐格的神话以及“赫尔佐格神话”
于我个人而言,赫尔佐格一直是一个谜团,哪怕观看再多他的作品,阅读了再多关于他的著作,有一个问题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赫尔佐格的电影,到底缘何具有那么强大的精神力量?是独具匠心的场面调度?是直抵灵魂的自然风光?是近乎绝迹的哲学思辨?抑或是无比强烈的征服*?
可能都是。但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奠定赫尔佐格电影基调和气质的宗教氛围。虽然赫尔佐格明确表示他现在已经远离宗教,但年轻时对宗教的狂热还是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一书中,他表示对童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两个记忆中就有一个是关于宗教的:他看到了一个男人“一身褐色衣服,没穿袜子,双手还油油的。他看着我,神情温和而慈祥,我马上明白了,这就是上帝本人!”虽然他后来意识到此人只是一个电力公司的工人,但这一经历无疑成为了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宗教体验。
应该说,赫尔佐格这一宗教性回忆和他与自然的亲密接触相叠加,将他引向了一种非偶像崇拜的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通观赫尔佐格的创作可以发现,超验主义的魅影从未在他的电影中消失过,以至于每当笔者观看赫尔佐格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爱默生和梭罗。赫尔佐格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崇拜,是神圣化、风格化的自然,另一种则是科幻,这种形式在《在世界尽头相遇》和《蓝星人怀乡曲》(2005)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前者以海豹那种类似地外信号般的叫声作为结尾,更突出了自然的未知和科学幻想色彩。

《在世界尽头相遇》剧照。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将赫尔佐格的童年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作为理解其作品的重要抓手,是因为他本人从不认为自己受到过德国任何重要思潮的直接影响,甚至否认自己作为“德国新电影四杰”的地位,同时又认为自己“从未被别人影响,但影响到了所有电影人”(见2018年3月赫尔佐格CFA讲座)。《批判性德国电影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German Film)认为赫尔佐格存在一种“自我神化化(self-mythologizing)”的倾向也绝非没有道理。但他并不是在虚张声势,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作品当中必定会带有其成长环境所独有的文化属性和特征,比如他在介绍自己作品时一定会提到的以想象力奇诡为特征的“巴伐利亚文化”。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称谓或许对他来说是虚无缥缈的,却也实实在在地从他的作品中显露出来——赫尔佐格酷爱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的音乐,经常提及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并以此强调其作品中的景观是“人物灵魂的外化”;他甚至直接颠覆了F.W.茂瑙的《诺斯费拉图》,用表现主义的布景、灯光和表演方式拍摄了全新的《诺斯费拉图:夜晚的幽灵》(1979);他将洛特·艾斯纳称作“德国新电影的教母”,而此人正是二战期间将德国电影转运至法国电影资料馆进行保存并研究的重要人物……所有这些都表明,赫尔佐格不仅对本民族地区的文化有着十足的认知,而且还清楚地意识到文化断代的可怕后果。从这个角度上说,赫尔佐格对自然、过往历史和民间故事的热爱,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德国的诸种文化传统而来。
如此看来,我们总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天主教的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以宗教本身为题材的电影《布道家》和《上帝的人生气了》(1983)之外,宗教性的角色无处不在,比如《阿基尔,上帝的愤怒》中声言“宗教总是倚靠强者”的神父,《卡斯帕尔·豪泽尔》中一心想让豪泽尔入教的神父等等 。赫尔佐格还经常使用宗教语汇来描述一种神圣的状态:他将自己早年的徒步巴黎之行(可以算是为洛特·艾斯纳祈福的旅程,《冰雪纪行》记录了他在这趟路程上的所见所闻)称为“朝圣”,把《在世界尽头相遇》(2007)里的水下空间称为“水下的教堂”,把提摩西·崔德威面对镜头的自我阐释称为“告解”,并认为他超越人的身份的想法,是一种“宗教性的体验”……
宗教之外,赫尔佐格也极其热衷在他的故事片中安排某种宿命式的预言。这些预言在赫尔佐格早期的电影中往往以梦幻朦胧的、极度风格化的影像呈现出来,比如在《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的结尾处,豪泽尔就讲述了一个“只有开头”的故事:一群在沙漠中迷路的年轻人在经验丰富的长者的指引下走到了城市,这无疑象征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但开放式的结局也无疑表明赫尔佐格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与之类似的是,《玻璃精灵》也结束于一只小船驶入大海,人类前途和命运未卜。
而在其后期的作品,如《儿子,你都干了什么》(2009)中,赫尔佐格则将他的宿命论和古希腊神话挂钩,形成了电影和戏剧的互文。有趣的是,这部影片的制片正是以神秘主义著称的大卫·林奇,只不过林奇的梦境是精神分析式的,而赫尔佐格则完全不相信心理学(他自称“一辈子也没做过几次梦,上一次做梦还是两年之前,梦到了自己在吃三明治”),类似梦境的预言可以说完全来自他的宗教情结。
如此这般,赫尔佐格的影片总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在经历了无数手大众传播之后,诸种神秘很大程度上又化为了他个人神秘的一部分。当我们讨论赫尔佐格时,神话和谣传的地位往往要高于真相,因为这既符合我们内心对于“大师”的期待,也恰好符合其影片所渲染的氛围。正如《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的作者保罗·克罗宁所言,“大部分你听到的关于赫尔佐格的事情都是不真实的。有关这个导演和他的影片所散播的无根据的谣言和彻底的谎话,要比其他任何在世或已逝的导演都多。”他的演员和伙伴克劳斯·金斯基(Klaus Kinski)固然也是这一神秘或神话的组成部分;二人构成的传奇甚至足以让人忽视赫尔佐格在电影创作过程中面临的种种艰辛。

《陆上行舟》剧照。
有趣的是,作为影迷的我们总是乐于探讨金斯基是如何在拍摄《陆上行舟》期间用枪对准赫尔佐格,像是在目睹两只灰熊互搏,或者亲眼见证疯狂的神明对战,却很少在意赫尔佐格是以何种惊人的毅力接受“天谴”,最终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丛林试炼”,并以此奠定了其在德国电影界甚至世界电影史当中无可撼动的地位。
诚然,赫尔佐格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奇迹。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对一切学院方法不屑一顾;他把自己当做一名匠人,却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需要成为一个崇拜对象。我们必须了解赫尔佐格,祛除他身上的重重幻影——他教会我们如何创作和生活,如何实现自己的雄心,如何看待创作与继承的关系,如何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看待世界。最终我们会发现,赫尔佐格的词典当中确实没有“追随”二字。他从来不需要追随者,也从来不去追随任何人的脚步,而这正是他得以“发明”电影的终极秘辛。
,